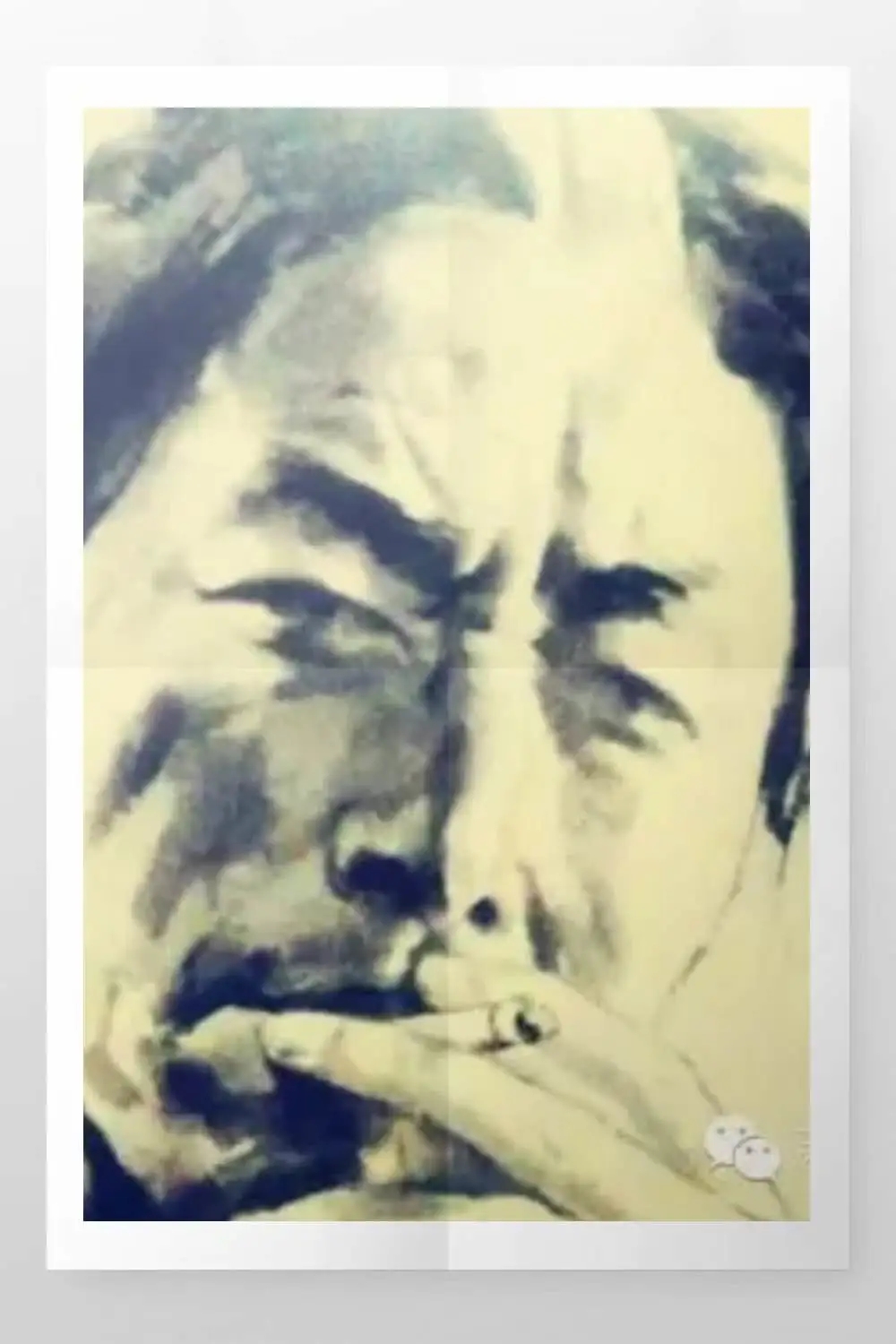绿岛年度自选诗(十首)
麦 子
守望最后一缕阳光
麦子在田野上
伫立成士兵凯旋归来的模样
麦子跋山涉水
趟过故乡沉默的河流
它栖息在岸边与新鲜的月光
对话
是锋利的麦芒刺破了田野
最初的一缕黎明
麦子殷实的表情
镌刻在父亲青铜一样的额头
就像高远的天空之上
那些沉重而质感的云朵
麦子入梦的子夜
镰在孤独地歌唱
陶罐理的阳光
带着斑驳的体温
沿着陶罐默默溢出的一段阳光
如青铜一般沉重
没有年代
也没有了呼吸
那时,我们在一首温顺的现代诗歌面前
友好而亲切地对视
我,选择了在一万米的地下努力地去
仰视
与你的目光并行不悖
神祇的指引
我们必将沿着幽深的巷道匍匐爬行
歌声穿越厚重的云朵
恰似血液游走于坚硬的煤层
一万年的守候
我们在生命的某个部分不期而遇
那时,我的父辈们
正在沸腾的掘场拿充血的目光
盗
火
子夜,抖落一地的 光
长成了矿工一根又一根倔强的肋骨
在陶罐里释放出一缕缕陌生的阳光
那可是我一万年前的骨肉兄弟
请把土地上疯长的诺言
收起 封存
完好地留给太阳后裔的子子孙孙
出逃的阳光在沉默的土地上踽踽独行
那个白垩纪的年代没有姓名
灵魂大盗
——致敬音乐
为什么 究竟是为什么啊
总有那么一只
神兽
在你的心头跳来跳去
灵魂被一根看不见的杵
捣
碎
它可以让你死
当然,也可以让你活
可恰恰就是在这一死一活之间
有一只神奇的偷手
却在众目睽睽之下窃走了你的
命
梦,在失火
[xyz-ihs snippet=”In-article-ads”]
雕 像
——再致鲁迅先生
我用目光去抚摸你的体温
在石头的内部
感受你最平静的呼吸
那是驱赶着灵魂的千军万马
踏破重重的关隘
一步一步走进你的坚硬的身体
有呐喊的声音轰鸣而来
由远及近
你说,为何不去重整旧的山河
抽出了最锋芒的那根骨头
做一根火炬
蘸着殷红的血浆与泪水
在布满荆棘的原野一路前行
一座血肉与钙堆积的碑
花花世界
白日梦不是 梦
是梦里醒着的游戏
白日梦也不应是梦
只因欲望的沟壑里遍野尸横
山野上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
看花的人总是来去匆匆
蝼蚁们为了争夺一块骨头
在沙漠厮上杀了一万年
大水连续三个月不退
汪洋之上鱼们在天空飞翔
欲望之城桃之夭夭
油头粉面的人们纷纷在草地上舞蹈
正人和君子们正在开会
研究男盗女娼为什么会生意兴隆
缺席的正义为什么总是迟到
冤死鬼们只能躲在各自的庙里睡觉
书上写的谎言已经长成了茂密的森林
杀人的刀面容慈祥恰似火烧的云
鬼们出入的街市灯火通明
而通往自由的巷道却荆棘密布阴暗潮湿
西装革履的匪徒热衷于掩耳盗铃的把戏
矿工们世代挖掘火种却死于太阳的阴影
文字们纷纷逃亡的子夜
被饿死的诗人们终于无家可归
粗犷的庄稼们在阳光下放声歌唱
那些跋涉的人们正趁着夜色匆匆赶路
打铁的人们默默抽出自己的骨头淬火
月光下他们把新的黎明锻打的通红
原本质朴的人们最终溺死于欲望之海
羔羊们依然安详地在山坡上吃草
夕阳的余晖照耀着苍茫的大地
一腔血色的记忆狂躁地在身体里奔涌
向日葵列队守护着土地的安宁
是谁用镰割掉了他们的头颅
一个诗人说今年的冬天很冷
另一个诗人说今年的冬天很疼
寒风凛冽的夜晚大地上呜咽哀鸣
凝寒的悲怆中我用疼痛的目光为母亲送行
人 间 烟 火
温一壶老酒
敬天敬地
最后再敬我们白发苍苍的
高堂
命,在日子里匆匆地奔走
光阴的岸边
堆积着欲望的尸骨
人的心如飞翔的翅膀 何以在
焦灼的土地上轮回
目光尚未落地之前
我们必将是一粒孤独的
尘
塚,在夕阳下窃窃私语
可我知道呵
那是些高尚的灵魂们在废墟上孤独地
爬行
蚂蚁们仍在厮杀
被腰斩的时光血流成河
温一壶老酒
敬天敬地
最后再敬我们白发苍苍的高堂
梦里驻着的千军万马
梦,是另一个世界
那里驻着我一个人的千军万马
那是沉重的青铜一样的天空吗
天空下乌云密布
有飞翔的骨头在自由地翱翔
电闪雷鸣过后
天空滑过一道道冷刃一样的目光
一万年的沉默
一万年的无语
所有的语言都将沉浸于石头的内部
从此,时光就不再坚硬
山河呜咽
如泣如诉
迷蒙中重现了丹青画卷里一幕幕
瘀血堆积的断层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 贺兰山阙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沙场秋点兵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 右擎苍
锦帽貂裘 千骑卷平冈
鬓微霜 又何妨 西北望 射天狼
——
叹如今,应有多少战栗的文字
在梦中乍醒
太阳红肿的眼睛在充血吗
那是妈妈在寒风中孤独的叮咛
漫卷的风沙里
为何望不见了男儿钢铁般的身影
欲,像一条巨蛇
它正在吞噬着一具具血肉之躯
色的钢刀
正如魔爪一般乱舞
到头来纸醉金迷终不过一场游戏
又怎一个“钱”字了得
一万年之后
还是逃不过啊 大江东去
人生如梦
一尊还酹江月
梦,是另一个世界
那里驻着我一个人的千军万马
秋 辞
那时,我们以军人的姿态行进在萧瑟的田野之上
长风以流云的方向在天和地之间
昭告着生命的威严以及目力所及的远方
黎明,每一颗草都在歌唱
就像一条浩浩汤汤的河流走过有梦栖息的故乡
望一眼长天的辽阔和浩然
我依然不能带走
白云的飘带遗落在长城脚下的羽衣霓裳
金色的阳光亦如单薄的蝉翼
我们像风一样跪拜于沉睡的泥土中央
让莽莽苍苍的荒原以原始的姿态向着天空说话
就像空空荡荡的流云向着太阳和月亮说话一样
那样的季节我们将用自己的声音
镶嵌着每一个血色的黄昏
秋风之上,我们从骨血里供奉那些
在乡村的小路上轻轻踩着炊烟行走的诗歌
星光下一片喧嚣的蛙鸣
起早远行的人们把露水装在了贴身的内衣
那是一路的泪水在与他说话
我们就是一群引颈南飞的雁阵
嘴里衔了最白的一片云朵
离开梦一样粘稠的热土,白山与黑水
还有我大梦方醒的古老的辽西
大漠古道的驼铃声里,男人们赶着驼队去了远方
那是高高隆起的古铜色的日头啊
多像田垄里父亲们深深躬下去的脊背
乾坤万物一片静穆
为什么不以秋风的名义席卷山川与大地
畅饮于江河湖海之畔遥看渔舟唱晚
饮千觞醉古今,萧瑟而蚀骨
冷眼潮头旁观尘世烟云,多少离合悲欢
只剩下了大江东去浪淘沙千古风云人物
何不一樽还酹江月
秋风一缕坦坦荡荡走过天地轮回
生亦何欢死亦何悲,在天在地而不在人
气爽天高萧瑟在前洒脱在后
既然如此那就把话都留在风中好了
上帝说秋天是个歌唱的季节
也是个说话的季节
在秋风里,生命就是瑟瑟的草
秋水是牵挂之后的惆怅吗
牵一缕前朝淡淡而清冷的月光最好
我们将以野草的名义
在窗花上画一个热烈而又灿烂的春天
给那些返青的生命
秋天是彼此交流和说话的季节
金黄的麦子在与阳光窃窃地私语
麦芒之上梦在舞蹈
向日葵有生以来就是一个沉默的汉子
被割掉了头颅之后
他依然用挺拔的躯干高挑着一轮红日
趔趄地走下山岗
大地以庄严肃穆的名义在为生命歌唱
庄稼与河流都已是流动的音符了
它们一起走下山岗
过了一条河就是外婆桥上的梦中的故乡
秋天在和一个季节自言自语
一只烤火的狼
把谎言的兽皮撕下来 或者扒下来
钉在墙上吧
因为今年的冬季风太大 天太冷
也好给良知的茅屋保暖
上路的老人和孩子们
成群结队
他们手里拿着一张滑稽的死亡证明
竟让天使的守门官们
怎么也无法看懂
死——于——基——础——病
那些匆匆忙忙去了天堂的人啊
活的已经懵懵懂懂
死的更是莫名其妙
看吧,这是个堆满了道具的舞台
角儿们各自在表演着不一样的自己
我是说一定要把谎言的皮
撕 撕 撕下来
该露出些怎样的心肝呢
那可是五彩斑斓的兽的花纹吗
走失的孩子已经
冻僵
叔叔要把它钉在风口出没的山坳
为你单薄的身体御寒
这个冬天真得很冷
我确定我就是一只穷途末路的
狼
瑟瑟地躲在荒原的腹地
靠捡拾亲人洒落一地的目光 烤火
歌唱吧,我梦中的云朵
你多像五月的麦田 始终保持着一种
金属般的沉默
神祇在大地上播种金黄色的阳光
向日葵的倒影可是殉道者
匆忙的脚步
而你灼灼的目光
曾经温煦着我们先人们 浑圆的
头颅
那就歌唱吧,我梦中的云朵
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你呵,在天空中飞翔的姿态
恰似一尾自由欢快的
鱼
从来都不带走一片童年的幻梦
那时我们手牵着手
去追赶一条忘我的河流
庄稼们也曾
在梦幻的魔盒里像神仙一样
跳来跳去
我们用生命守候着秋天里
一阵阵骨感的风
坚定地走过两个人的宫殿里金碧辉煌的
地老和天荒
那些年,被我们热恋的诗歌
曾是猎人枪口下仓惶出逃的猎物
而你
却用一颗温柔的子弹 无辜地
击中了我疲惫的 心
歌唱吧,那可是我们自己的天空啊
况且还有那么多
被放牧着的自由自在的云朵

![]()
新西兰 澳纽网出品
编辑:小图
633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