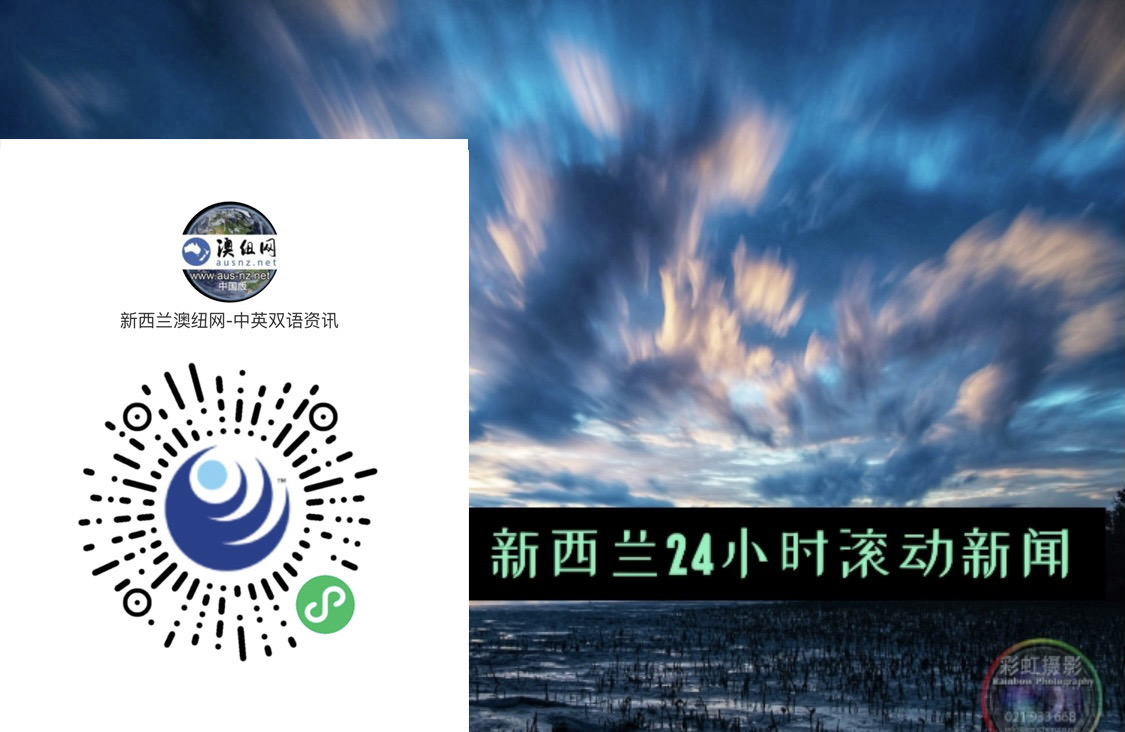断绝关系
若曦已经两年没和父母说话了。
两年前,父母以旅游为名,把她骗去“大爱无疆”游学营,一个宣称可以治疗青少年抑郁症、强迫症等问题的民间机构。在那里,她遭遇两次殴打,被强迫跪下磕头,最后写下和父母断绝关系,以及“是死是活和‘大爱无疆’无关”的协议书。没有手机,没有钱,她攥着这两张纸和身份证,沿马路走了一夜,从位于草原的营地走到赤峰市区,找到了救助站。
从那之后,她一直独自住在家里的老房子里,并退出了所有的家庭微信群。
曾经的官网介绍显示,“大爱无疆”由居裕然创办,让“200多个被专家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自闭症、狂躁症、精神病等疾病而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的孩子,断掉药物,找回自我。” 曾参加游学营的家长介绍,一次游学营学费9万元,承诺父母和孩子都可以直接与居裕然对话,终生服务。
但很多参加过游学营的孩子不这么认为。一个15岁时确诊双向情感障碍的女孩2019年11月参加了游学营,由于看不惯在那里所有孩子要叫居裕然“爸爸”,以及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她激烈反抗,“被打得很惨”,连报了3次警。
2020年5月,岳明菲从自己的病友那听说了“大爱无疆”,决定要联系心理机构进行“反洗脑”。她联系了近20位受害者,记录他们在“大爱无疆”的经历。这后来发展成一场集中曝光。
2020年,红星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传销嫌疑人居裕然出狱创办“大爱无疆”游学营,有学员爆料,该游学营以教育为名对孩子家长进行洗脑控制,其间对学员进行殴打,给抑郁症学员强制停药。甚至有孩子抑郁症发作,工作人员却劝他去死,还被当作成功治疗案例宣传。2020年5月2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江苏盐城市盐东派出所获悉,派出所接到“大爱无疆”游学营学员报案,已立案调查。5月7日,居裕然称,他之后不再举办“游学营”,不再收学员。
至今还有家长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分享着在“居爸”带领下,女儿休学3年成功复学的经历——“《居说集》(居裕然语录集——记者注)真是个系统、正确、有效的家庭教育理论。坚信裕然文化,居爸能救我家于水深火热之中。”还有母亲在讲述如何践行“大爱无疆”的理念——托举老公,女人退后。
从游学营回来后,秦杉杉也几乎和父母断绝了关系。如今她独自生活在武汉。很早就因病休学,没有文凭,为了养活自己,她先后做过餐厅服务员、便利店店员。她和父母鲜有联系。秦杉杉如今看到光头、壮硕的男人就觉得恶心和恐惧,那样子很像居裕然。
“大爱无疆”也是压断若曦和父母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不想再跟父母有什么联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试图跟他们沟通,都没有什么用。”
若曦曾经成绩优异,在班里排第二名。但高一时她因为强迫症和焦虑症休学,如今24岁了,没有上学,也没有工作,和过往的同学也没什么联系。这两年里,每天和她说话的是楼下的摊贩。煤气灶是坏的,她有时下楼买点东西吃,有时就不吃。父母来拿过几次东西,他们不说话。如今他们仅有的联系,是父母时不时发来300、500元的转账。曾有父亲那边的亲戚来找她,说服她去自家书法培训机构做老师,算是一份工作。她挺高兴,后来才知道原来亲戚一直把聊天记录转给爸妈看,“是串通好的”,她就没有再干下去。

资料图片:抑郁症患者。张楠摄
画面重现
被骗到“大爱无疆”第一个早晨,若曦就因为“看起来很嚣张”被打了。那之前,她在二楼看到几个人拿着“戒尺”打一个男生,数着“一二三四”。她拿手机录了像,对男生说“我回头帮你发网上去”。一个“大爱妈妈”冲到她跟前,“父母是天,孩子是地,男人是天,女人是地。”若曦狠狠将这个女人推开。
若曦回忆,居裕然打她时,先拿出戒尺打,一边打一边问“服不服”,她说不服,就继续打,最后她只好说服了。旁边围了很多人,父母都在场。居裕然又让她父亲打她。父亲的手直接冲她的脸扇过来。“我能感觉到,他早就想打我了,但是他觉得打我不好,因为我一直都说你不能打我。到了这里,他突然有底气了,因为居裕然支持他,他能放得开了。”
那一刻若曦才想到,童年时这样被打的场景发生过很多次:她仰面躺在地上,父亲则是站着,他打完就走了,过一会儿她才能站起来。这是父亲一贯的教育主张,“孩子就是要打,越小的时候越应该打,不然就学坏了。”
若曦觉得居裕然和父亲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们都认为这不是殴打,这是惩戒,这是一种手段,不是暴力。他们都会在打完又用其他方式“拉拢”你,比如满足你的物质需求。他们都常说自己很厉害。居裕然常说他的势力有多么大,说每年有多少人给他送东西,有多少人喜欢他,崇拜他。
那天被打后,她不愿意跟着大家坐车去观光,于是直接被4个人从房间抬了出来,放在地上。有个“大爱小子”来劝她,说自己一开始来的时候也被打,但被打完之后就喜欢上这儿了,还说,如果她不上车,他也会被打。若曦无奈带着身上的淤青坐上了车,中途因为应激反应下车呕吐。晚上,营地举办了篝火晚会,让孩子围成一个圈自我介绍,每个人唱首歌。父亲非得让她跟他一块去跳舞,她没去。对那天父亲打她的事,父母都没有道歉。
若曦也知道,父母把她带到“大爱无疆”是因为束手无策。在休学的两年中,她经常跟父母闹,最后发展到动手打人。她打起人和父亲一样手重,一年春节把父亲的头打破进了医院。
在那个过程中,她理解了家暴者的心理,打完之后她常无法面对自己,没有办法承受自己的愧疚,于是为了缓解这个愧疚就又打人。但若曦知道自己的心结在哪儿:“我那么强硬,是想让他们知道打我是不对的。”但在她看来,父亲只是面子上会道歉,或只说自己的处理方式有问题,但他从不真正承认自己是错的。
游学营第二天,因为若曦仍然不配合集体活动,又被几个“大爱妈妈”拿着戒尺打了一次。后来,居裕然要求若曦给父母跪下道歉,“说对不起,我错了”。“很强硬的,你不得不去服从他,不然他又要打我了。”于是她照做了。听到她说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母亲哭了,“看起来很感动的样子”。
若曦觉得居裕然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他演讲非常接地气,会讲他女儿,像拉家常一样,很江湖气,把人当兄弟,对于打人骂人,没有任何掩饰。但警察在的时候,他和其他工作人员——那些被称为“大爱爸爸”“大爱妈妈”的人,是绝对不动手的,也不会拿戒尺。游学营的几天里,数次有人报警,一个警察在车上陪了若曦一段,“他们一直都是老老实实,警察一走,马上就亮出来戒尺。”她还听到,有次警察走了之后,居裕然说那些警察都是畜生。
也有人觉得这些描述太夸张了。林敏霞带儿子参加过游学营,她看重的是,活动过程中,居裕然会去观察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他觉得不妥的地方,把它给指出来。“别的没什么特殊的东西,我们那一期比较平淡的。”
她只见到过一个孩子当众被打,也是用戒尺。起因是孩子在吃饭时间在房间里看电竞比赛,违反了规定。开营第一天,有个被哄骗来的初一女孩报警,“警察去了一下说了几句就走了”,女孩子后来也就跟父母一直待在那里。
秦杉杉的父亲曾是反对打孩子的人。参加完游学营后,秦杉杉发现,父亲变得像居裕然一样了,吵架时常说,“请你注意和我说话的态度。”父亲做了一些给她“留下一辈子阴影”的事。比如把她推搡在地上;比如扇她耳光;比如曾把她手指打骨折,去医院打上石膏后,又把石膏打裂。
一次冲突中,父亲把她反锁在房间里打她。秦杉杉情急下拿出小刀想自卫,结果是左手虎口被父亲划开。血止不住流,她一个人打着伞走了30分钟到医院,“手上都是血,医生说切得再深一点,左手就废了。”如今讲起这件事她仍忍不住哭,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秦杉杉只要看到男性,都会觉得厌恶。

资料图片:抑郁症患者。张楠摄
乖孩子
2020年5月,岳明菲联系了近20位受害者,在接触这些人的过程中,她发现多数病友,都是很乖、很勤奋,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林敏霞在儿子高考后发现他“会说一些匪夷所思的话”,比如把自己想象成日本动漫里厉害的角色,说自己有特异功能。她当时觉得儿子“脑子有病了”。直到经过心理咨询师提示她才明白,那是因为儿子始终无法达到她的要求,才把自己幻想得无所不能。于是她想到,这个生病后会打她、摔东西、会在公路上下车逃跑的儿子,一直是多么努力地试图达到她所有的期望。“他想努力做一个好孩子,爸爸妈妈想让他做到的,尽管他做不到,他也努力去做。”
初三时,若曦在一次重点高中的提前选拔考试里落选,那时起她发现自己变得“不正常”了。
翻卷子的声音,班级里说话的声音,在她脑子里嗡嗡响成一片。她希望自己时刻保持坐姿“挺拔”,却“感觉怎么坐都不对”,等到突然回过神,意识到一天都没有听课,一直在调整坐姿,一下子后背生出冷汗。
这种无法学习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高一。若曦没有把这种状况告诉父母,直到名列前茅的成绩退步到倒数几名,父亲大发雷霆。
她从小就不会在父母面前哭。他们看到了她哭,会生气、不耐烦。“现在想想我经常崩溃,从小经常自己哭,不敢让他们看见,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发生的,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高一上学期结束,爸爸才意识到,女儿需要去看病了。
岳明菲自己是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小时候妈妈不让她哭,所以她只会哽咽,不知道怎么哭出来。“妈妈是医生,看到我流泪,她就会拿一个针筒吓我。”在她看来,“你小时候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情绪相处,长大了积累了太多情绪,一下子就崩溃了。”
走投无路
在走进“大爱无疆”之前,几乎每个家庭都尝试过用现代医学手段解决问题。
林敏霞感觉到儿子不对劲之后,第一反应是去了上海一家医院,量表结果显示重度抑郁,医生开了药。吃了4个多月,孩子症状越来越重,在家里摔东西,打人,自残,很难控制。
若曦碰到过像审犯人一样的70多岁的心理咨询师。家长说她不按时睡觉,不爱出门不洗头不洗脸。咨询师说,你就列一个表格,把每项都写上,一项一项做。“这是给你留的作业,下次把那个表格拿上来给我。”“你不是不洗脸吗?你要督促自己。”咨询师特别严肃,像个老师:“你有什么梦想没有?你要确定你的理想。”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有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的检出率为7.4%,检出率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升高。
“渡过”平台的咨询师邹峰见到过太多在求医道路上无助的家庭。“青少年抑郁症越来越高发。他们精力旺盛,大脑皮层没有完全发育好,理性思维能力不完整,所以焦虑导致的一些行为易被误以为是双向情感障碍症状。精神科医生,包括一些老专家,容易把成年人的标准和经验用于青少年。”
在他看来,目前青少年抑郁症治疗上,就算在大城市大医院,也很难解决问题。他能够理解那些选择“大爱无疆”的家长,“家长的核心问题在于觉得别的都没用。”“走投无路,现在有人大包大揽,你就会相信他有用。交的钱越多,越是会被他洗脑。”
岳明菲很理解病友的感受。她在纽约读大三时患抑郁症,严重到没有力气坐起来,会把热油故意溅在自己手上。经过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的共同治疗,她用一年半时间恢复了正常生活,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
她说,学校医院共有四层,有一整层都是做心理咨询的。由于每个咨询师奉行的理论体系不同,治疗方式也有很大差异,觉得咨询师不合适,可以换,直到换到满意为止。她是换到了第四个才觉得有效了。
她同时有3位医生,分别叫Therapist(心理咨询师)、Doctor(医生)、Psychiatris(精神科医生),每1-2周,她跟3个人分别见面聊一下最近的状况。而医生之间每周会交换一下信息,商量给出药物的修改方案。测量表是非常辅助的工具,每5次治疗,会重新做一次测评,用曲线图给出一些因子的分析。医生会给她分析,某个分数下降了,或某个分数没有变,“我们应该从哪里继续努力,怎样一起改善。”所有的治疗费用,包括心理咨询师那部分在内,都可以走医保,“药只要服务费就可以了,10美元左右。”
“医生不会单纯给你开一把药,会跟你解释,我给你开这个药是什么用的。比如最近没有力气,他会说,这个药也许会给你多一点能量。吃了之后,下周会跟你聊,你觉得最近有力气刷牙了吗?”
2020年6月岳明菲回国后,在上海杭州都找过“最难约”的专家。但给她的感觉是,“你反正就是抑郁症,开药,开完就走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心理科的主治医师曹新毅在医院既负责药物治疗,也会做心理咨询。他说,他觉得目前国内治疗体系很大的问题是,大部分地区心理咨询费不纳入医保,一小时几百元的咨询费用,长期来看,很多家庭承担不起。
无助和这种“承担不起”让他们寻求其他的帮助。
林敏霞回想起自己是如何被“大爱无疆”说服的。她当时在群里潜伏了一年,每天群里都会转发一些文章,讲孩子经过“大爱无疆”的帮助如何恢复正常。“逐渐就会建立起信任,家长都是在一种很焦虑的情况下,都是逼得没有办法了。”
若曦的妈妈最早接触“大爱无疆”时,父亲也表示反对,觉得像“骗老年人”的东西,但是后来父母一块去听课,回来说“可能真有用,那里的孩子都特别好。”

资料图片:抑郁症患者。张楠摄
家庭治疗
岳明菲在接触“大爱无疆”的近20个受害者时,发现每个家庭的问题各不相同,比如家暴、父母本身就有抑郁症等。而共同点是,这些家长都完全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会痛苦。“他们觉得我已经给你够多了,你有什么好痛苦的?”曹新毅说,他们行内有句话,“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的问题。”
孩子出现问题后,林敏霞不停在学习,发现几乎所有心理学课程指向的都是家庭。“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忽视了很多方面,是我们自己的认知没有达到的方面。”
她形容,儿子从出生到生病,一直生活在一种“乌云压城”的气氛中。丈夫脾气暴躁,全家人像围着一颗炸弹。当时她不知道该如何承受这种氛围,没有考虑改变,选择用工作去逃避。而孩子比她更敏感地吸收了这一切。她回想到,孩子上初中时就说睡不着觉,实际上那时“他眼睛就会流露出仇恨的样子”。
若曦总觉得,父亲的强迫倾向比她更为严重。记得有次他买台电脑回家,突然就不高兴,说电脑的屏幕不对称,还拿尺子去量,发现左右差一两毫米。若曦常看到父亲在家里摆弄物品,那种时候,“仿佛一头猛兽在那儿,打仗一样的状态”。
她曾经特别希望成为父亲那样的人。他是国企的干部,曾是老家唯一的大学生。父亲懂得多,思想活跃,她很渴望和他交流。刚进入青春期时,她每次提出一个新的想法去跟父亲讨论,他都会说“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然后用他40岁的经验、阅历来跟她比,“肯定是我完全比不过他”。父亲总会把话题绕到他自己身上,“会说你们之所以这样,就因为没有像他那样”。那个时候,她在日记里写:“我以前总认为我是一个什么独一无二的人,原来根本就不是。”
父亲常说自己读书时怎么努力,讲当年某些人瞧不起他,提起这些还是咬牙切齿的样子。在她眼里,父母关系糟糕。他们会跟她互相抱怨,“有时候我觉得有点愧疚,都是一家人”,于是会帮另一方说话,父母会嫌她跟另一个人更亲近。
若曦有一个上中学的弟弟,彼此很少有交流,她很久没去看过,“我都要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弟弟也害怕她,因为小时候会被她打。
回忆起童年,她始终觉得自己对父母来说可有可无。有一次她从姥姥家回来,突然发现家里收拾得特别干净,妈妈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开心地看电视,“我觉得没有了我,我妈过得特别自在,但是有我,她好像总是不开心。”
生病之后,若曦觉得“不要那么不关心我了,我都这样了,我都生病了”。当时他们去医院做心理咨询,会单独跟孩子谈,再跟父母谈。但谈完了,父母私底下从来不会跟她说什么,像走一个流程。“为了给你看病而看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她觉得,好像给她看病,是为了让她赶紧变得像个正常人一样,赶紧上学,然后再好好学习。
秦杉杉记忆中,妈妈总是很焦虑,小学二年级就因为逼她背英语,用绳子把她绑起来,用衣架打她。而爸爸总是不在家,每天都有应酬,唯一见到他的时候,是早上她出门,他还没醒的时候。
生病之后,他们找了心理咨询师聊了一两年。每周都去,每次都花好几百元。但“一点用都没有”。她觉得没用的原因是妈妈不配合。咨询师把三个人叫在一起聊了之后,说问题主要出在妈妈这里,希望妈妈能来做行为矫正治疗。秦杉杉的妈妈说,“我的问题我自己会调节,你把我女儿解决好就行了。”
林敏霞已经意识到自己也要参与到治疗中。“自责愧疚的情绪,我用了5年时间才走出来。家长抱着这种想法的话,对孩子的康复也是不好的,会做出一些非常焦虑的举动。”她和丈夫也不间断跟咨询师沟通,请咨询师指导他们该怎么做,“药物这块我觉得帮助是短期的。”经过这样长期的咨询和被纠正的过程,现在她感觉到,儿子觉得爸爸妈妈是可以信任的。

资料图片:抑郁症患者。张楠摄
重新去爱
若曦说,她曾经想当个科学家,搞科研造火箭。但现在,很多东西对她来说太遥远了,她甚至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她在努力把现在的生活过好,积极锻炼身体。如今她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心理咨询师,“有人文情怀,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她不再和父母相处,但她说,在她心里,住着一个虚幻的父母的影子,她会和这个影子交流,和内心的父母达成和解。
秦杉杉说她独自在外,不会牵挂父母,但有时候看到阖家团圆的场面,“心里不难过是不可能的”。有人问她,将来你会不会像你妈对你一样对自己的小孩?她回答不会,但小孩太麻烦了,应该不会生小孩。她对婚姻和家庭从来没有过渴望,19岁生日,她许的愿望是,永远做一个快乐的单身女孩。
林敏霞看着单位里的年轻人对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提出很高的要求,把自己的脾气随意发泄在孩子身上,觉得他们在重蹈覆撤,“我希望我经历的痛苦,别人不要再经历。”她在想如果儿子小时候,很逆反,很会保护自己,可能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她如今不再避讳提起孩子的病,有相似经历的家长找她来取经,她会说,“你真的能放下自己的期待吗?”她说,孩子以前就是她挣面子的工具。“现在你放下这些的时候,孩子他真的能感受到。”
她觉得相比让世界上“大爱无疆”这样的机构消失,更重要的,是让父母停止伤害孩子的行为。
邹峰2017年加入“渡过”读者社群,这是一个精神健康方面的科普账号。他发现很多读者其实是家长,后来“渡过”成立了家长群,七八个群迅速建满,比那种成年抑郁的患者更多,参与更积极更迫切。
邹峰在“渡过”第一期“亲子营”讲的第一堂课,叫《表达与看见》。“表达就是疗愈,看见就是疗愈。孩子要多表达,父母要多看见。”看了那么多家庭,最后他的结论是家长一定要接受真实的孩子,不要去把他理想化。而孩子不要把家长的要求内化,把自己理想化。
林敏霞想象,自己要重新开始爱孩子,就像回到他刚刚出生时那样,用能想到的最好方式去爱他陪伴他。他们的心理咨询终于走上了正轨,彼此好长时间没吵架了,“我觉得找到了方向。”
现在她会经常回想起,以前她带两三岁的儿子去市里的公园,只要他想玩的都去玩,过山车、碰碰车。那时的儿子很快乐、很单纯的样子。
秦杉杉现在觉得很后悔,觉得童年时期太顺从妈妈。她很爱阅读,喜欢逛书店,她想,如果童年时能把很多的时间拿来看书,或者出去锻炼身体,就会快乐很多。她还喜欢弹钢琴,弹钢琴的时候会感觉内心很平静。
如果回到小学二年级,妈妈再次强迫她背单词的时候,她会说,我不。
(文中若曦、秦杉杉、林敏霞、岳明菲为化名)
来源: 冰点周刊
2,734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