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读者文摘
“老牌淑女”浅析
作者: 秋阳 人气: 日期: 2004/7/10“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这段文字,刻在一座墓碑上,死者名叫川嫦,是张爱玲笔下的一个女孩子。照理说,字是石刻的,碑前还有石头天使守护,上面的话便有了永恒的定义。然而,就在作者娓娓地完成了这一番如呤如诵的记述后,笔锋一转,发出了一声苍凉的呼喊:“全然不是这回事。”
随著陈乃珊、陈丹燕的几本书飘扬过海,现在的北美华人,也津津乐起上海“老克勒”和“老牌淑女”来了。上个月,晨报用了一个版面介绍了“时髦外婆的前世今生”,文章声称:“她们是全中国淑女的标本,是这一代中国人民渴望小康的动力。”
评价之高,连我这个在上海土生土长的人都有点坐不住。打了个电话给母亲,如此这般地把报上内容讲给她听,母亲失声笑道:“不敢当,不敢当哟。”挂上电话,耳边响起张爱玲的声音——全然不是这回事。
地域
首先,上海淑女本身有强烈的地域范围,基本上缺乏代表性。上海人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套心理文化方式。也就是余秋雨先生提出的上海文明。对于女人味的审定,更为明显。
巩俐的风韵无可置疑,但她在“摇到外婆桥”里,要演一名叫小金宝的上海舞女,则完全乱了方寸,被讥笑为“一个扭屁股的北方妞儿。”(请注意:上海女性扭动的是腰肢)。徐帆在话剧艺术上的造诣可圈可点。她主演的话剧《阮玲玉》,在北京好评如潮,但舞台搬到了上海,却遭受冷落,叫人跌破眼镜。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出》中的陈白露。其实,曹禺的剧本并没有限定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哪一个商坞,特别是其中第三幕,妓院的描写完全按照北方的情形。然而,一九五九年,著名演员白杨出演了女主角。一下子,上海人认准了,那个妩媚而又凄然的交际花就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十里洋场的尤物。文革后,《日出》一演再演,却再也找不出这么一个陈白露来了。谢芳的话剧,方舒的电影,按照她们的经历和程度,能演到那样,也真难为了她们了。但上海观众的评价却异常苛刻:“说不清爽,就觉得缺脱了一口气。”
艺术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现实生活的提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他的表演体系规纳为演员的自我修养。“修养”无捷径可寻。所谓上海人的修养,好坏不由吩说,是由此方水土风情孕育而生,单靠模仿,难以奏效。举一个最不上台面的例子,还是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振保的太太因为心情关系,得了便秘,上一趟马桶就是半天。这一段写得活灵活现,每每读到此处,熬不住要笑,心里说,也只有她啦,把个上海女子上厕所都写得如丝如扣,特里特别。
鲁迅对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有这么一段文字,说她们“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在喜欢,也在恼怒。”
真是对上海女子的神情的一个绝妙的概括。
阶层
如果把地域观念作为横标的话,阶层关系可以作为解析的一根纵轴。淑女决非人人能当。在上海妇女中占绝大多数的女工,理所当然地被摈弃在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被蔑称为白相人嫂嫂,流氓嫂嫂和亭子间嫂嫂的下三流女人,自然也上不了台面。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但没有专门提到女人。女人和知识份子一样,是没有阶级的。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她们的身份随“老公”而定。早在满清时期,上海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校,就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解放前,上海有几所名牌大学设有家政系。市三女中的前身,还为高中生开了家政课。市面上戏称为新娘学校,是为小姐们转换身份当少奶奶作准备用的,少女当了“女结婚员”便有了立脚之地。听说,现住在芝加哥,有一位老太太,年轻时就穿过这付袜统。花卉装饰,调酒烹饪,京昆票房。一呱两响,无所不精;待人接物,应付各种场合,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凡于她有过接触的人,均都叹为观止。这就叫本事。
然而,淑女的弱点也由此而生。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她们的人生是为了当妻子,在那她们的世界里,也就只有了丈夫和孩子,避免不了的狭小和逼仄。她们在经济上不同程度仰仗丈夫,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独立地位,成为附庸,枷锁架在脖子上,她们的背总是弯的。娜拉离开玩偶之家,门可以关得砰砰响,但倘若她不离开淑女的位置,不过几天,她还是不得不回来,恳求她那位虚伪入骨的丈夫原谅。再有,这类女性确有风度,确会耍风流,有极好的应酬功夫。但她们缺少真切的感情交流。一言一行,都有‘笑不露齿、怒不高声“的框订。笑,只不过笑给人家看的;哭,却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朋友呢?结了婚后很难接识到新的朋友。在一道操操麻将,结结绒线,看看电影,听听绍兴戏,谈谈山海经的人倒是有的,不过都是打发自己生命的陪伴罢了。这群女性们知书达理,能领略琴棋书画,却不多自己的才学,不具备本人的思想锋芒。有的小姐,即使曾经光彩照人,捧为校花。只要一踏进淑女的怪圈,无需多久,便成了明日黄花,留下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哀叹。张爱玲、苏青等旷世才女,辉煌鼎盛时期不过两到三年,原因要复杂得多,但都与她们的婚姻状况有关。
所以,在对淑女的认可上,市俗订立的标准就显得有几分怪异。譬如,国母宋庆龄女士,其母是上海老祖宗徐光启的后裔,她本人在上海出身、成长。到老话语中仍带有浓厚的乡音。按理说,不管从哪个角度,夫人应为所谓淑女的当之无愧的领袖。然而,上海人不敢提这个。夫人拥有太深切的喜,太深切的悲,对社会有太杰出的贡献,对儿童有太博大的情怀。她们实在承受不了她。同样,对于蒋夫人宋美龄,人们也不可能将她规纳在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否可作这么一个设想。那一位三十年代混迹上海的明星蓝苹小姐,既会“嗲”,又会“作”,三缸水可以搞得六缸浑。弄得男人要死要活的。趟若她后来没有被放出来,祸国殃民,最终被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她能不能挤身于淑女之列呢?你去问问看,我想,上海人又要撇嘴摇头了:“不要触人酶头了,伊算啥末是。”
记不得是程乃珊还是陈丹燕说过的,上海淑女的最大特点是:中庸而别致。在我看来,倒讲得蛮在点子上。
时代
一九四九年五月,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上海被解放。妇女的命运出现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一小部分人走了,去台湾,去香港,甚至还有远度重洋,另处落脚的。但大部分人,依然留在本土,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不管是走是留,均为“随从夫君”。老牌淑女的时代也就此结束。留守的女子们,有了她们的新称号----家庭妇女。在弄堂里,互相见了面,都称呼为“某大姐”。一个个,非常迅速又非常自然地收敛了以往的光艳,脱去了旗袍,穿起女式列宁装来了。再后来,一个个,走出了家门,到社会上谋求职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家中开始发生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为摆脱“家庭妇女”的落后名声。到底都是有文化的,学校里学的没有白白浪费,有的到医院作药剂士,护士,有的当了写字间的秘书,还有的,被分配到小学校当代课老师,踩著风琴的蹋脚板,带领孩子们唱:“我有一双万能的手,万能的手。样样事情都会做,都会做。”
妇女的解放,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件好事。然而,一个巨硕的然而紧紧跟在了后面。鸟儿飞出了笼子,迎接她们的却是无情的疾风暴雨。接下来三十几年的生活渐渐地变得疙里疙瘩了。新社会,社会风气和文化观念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们要买帐,要承认落后,要改造,要靠拢领导,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对此,她们并不在行,但不得不学起来。有人不惜下了档次,唯唯若若,跟着戳壁脚,搬弄是非。不然的话,就连她们的亲生儿女都看她们不起,“跟你们划清界限”
是她们最怕听到的话,听了心要碎。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她们的男人们都成了特务,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被打翻在地,再蹋上一只脚。女人呢?圣经上说,女人有罪是因为偷吃了依甸园的苹果,这些与夏娃同样简单的女子,甚至还没有那样“不良”或“不从”的念头呢。可是罪名是少不了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身攻击和侮辱也因此大显身手,其中最耳濡目染的是“化作美女的毒蛇”。话是从毛主席语录来的,这一处倒与圣经一脉相承。蛇的本质是引诱,男人变坏,女人是祸首。既然罪名这般定了,当然地成为了革命对象。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毒蛇”们的招架能力又极其单薄,甚至要辩解,腿都会抖,舌头会打结。她们只能认了。一场革命,革得她们莫名其妙,革得她们面目全非,革得她们做梦都不敢做她们的“那个失去了的天堂”。《上海生死录》的作者郑义女士,在被逼到绝壁时,只剩下一丝希望,她要比毛主席活得长,只有这样,她才能翻身。这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女性,她熬过来了。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成为了历史。
今日,小资又弥漫著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据说,在上海的舞厅里,偶尔还会碰到屈指可数的几个老克勒,自以为是又自得其乐地带着女孩子蓬嚓嚓;在公园的英语角,也是这几个人,自说自话又自鸣得意地纠正年轻学生不够“克勒”的英语发音。这些人的年龄,怎么说,都在七十五岁以上,但全是男人。美女们呢?基本上都隐没了。女人的寿命可以比男人长,但她们展现于社会所受到的袢索,比男人多的多。况且,女人对世事的参与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热情。花样年华早已不在,留恋带来的只有伤感。何必不安分,何必要“作”,受人耻笑呢。她们又回到了她们的“笼子”,轻轻地掩了门。窗外有月亮的时候,看著月亮,隔著几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没有月亮的时候,她们感觉恍惚进到了坟墓,她们在静静地等候……
现在,市面上今所宣传的时髦外婆,实际辈份比老牌淑女要低,其代表人物为退休的上海人艺演员周谅量,她曾在黄佐临导演的影片《黄浦江的故事》里,出任女主角。很美,演技也有份量。与她同时代且出名的有祝希娟,曹雷,严丽秋等人。在解放时,她们还未到“杨家有女初长成”的年龄,在解放后受的高等教育,在新社会成长,比起上一代,她们要从容得多了,起码,她们不会只是抵挡。她们的苦恼是她们的青春年华丢失得太没有名堂了,也不甘心就这么老去,她们拾起了时髦。
淑女的隐没是极其自然的社会现象,找不回来的。近几年,市面上又可以见到一些三四十年代的月份牌,阴丹士林布的商标纸,双妹牌爽身粉的罐头,说是古董,又不算古董,你可以从那儿看到她们的倩影,千篇一律的细细的腰,甜蜜蜜的笑,眼泡都是肉鼓鼓的,阮玲玉的模式。“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
又全然不是这回事!
随著陈乃珊、陈丹燕的几本书飘扬过海,现在的北美华人,也津津乐起上海“老克勒”和“老牌淑女”来了。上个月,晨报用了一个版面介绍了“时髦外婆的前世今生”,文章声称:“她们是全中国淑女的标本,是这一代中国人民渴望小康的动力。”
评价之高,连我这个在上海土生土长的人都有点坐不住。打了个电话给母亲,如此这般地把报上内容讲给她听,母亲失声笑道:“不敢当,不敢当哟。”挂上电话,耳边响起张爱玲的声音——全然不是这回事。
地域
首先,上海淑女本身有强烈的地域范围,基本上缺乏代表性。上海人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套心理文化方式。也就是余秋雨先生提出的上海文明。对于女人味的审定,更为明显。
巩俐的风韵无可置疑,但她在“摇到外婆桥”里,要演一名叫小金宝的上海舞女,则完全乱了方寸,被讥笑为“一个扭屁股的北方妞儿。”(请注意:上海女性扭动的是腰肢)。徐帆在话剧艺术上的造诣可圈可点。她主演的话剧《阮玲玉》,在北京好评如潮,但舞台搬到了上海,却遭受冷落,叫人跌破眼镜。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出》中的陈白露。其实,曹禺的剧本并没有限定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哪一个商坞,特别是其中第三幕,妓院的描写完全按照北方的情形。然而,一九五九年,著名演员白杨出演了女主角。一下子,上海人认准了,那个妩媚而又凄然的交际花就是不折不扣的上海十里洋场的尤物。文革后,《日出》一演再演,却再也找不出这么一个陈白露来了。谢芳的话剧,方舒的电影,按照她们的经历和程度,能演到那样,也真难为了她们了。但上海观众的评价却异常苛刻:“说不清爽,就觉得缺脱了一口气。”
艺术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现实生活的提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他的表演体系规纳为演员的自我修养。“修养”无捷径可寻。所谓上海人的修养,好坏不由吩说,是由此方水土风情孕育而生,单靠模仿,难以奏效。举一个最不上台面的例子,还是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振保的太太因为心情关系,得了便秘,上一趟马桶就是半天。这一段写得活灵活现,每每读到此处,熬不住要笑,心里说,也只有她啦,把个上海女子上厕所都写得如丝如扣,特里特别。
鲁迅对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有这么一段文字,说她们“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在喜欢,也在恼怒。”
真是对上海女子的神情的一个绝妙的概括。
阶层
如果把地域观念作为横标的话,阶层关系可以作为解析的一根纵轴。淑女决非人人能当。在上海妇女中占绝大多数的女工,理所当然地被摈弃在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被蔑称为白相人嫂嫂,流氓嫂嫂和亭子间嫂嫂的下三流女人,自然也上不了台面。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但没有专门提到女人。女人和知识份子一样,是没有阶级的。女人是男人的肋骨,她们的身份随“老公”而定。早在满清时期,上海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女校,就是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解放前,上海有几所名牌大学设有家政系。市三女中的前身,还为高中生开了家政课。市面上戏称为新娘学校,是为小姐们转换身份当少奶奶作准备用的,少女当了“女结婚员”便有了立脚之地。听说,现住在芝加哥,有一位老太太,年轻时就穿过这付袜统。花卉装饰,调酒烹饪,京昆票房。一呱两响,无所不精;待人接物,应付各种场合,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凡于她有过接触的人,均都叹为观止。这就叫本事。
然而,淑女的弱点也由此而生。无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她们的人生是为了当妻子,在那她们的世界里,也就只有了丈夫和孩子,避免不了的狭小和逼仄。她们在经济上不同程度仰仗丈夫,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独立地位,成为附庸,枷锁架在脖子上,她们的背总是弯的。娜拉离开玩偶之家,门可以关得砰砰响,但倘若她不离开淑女的位置,不过几天,她还是不得不回来,恳求她那位虚伪入骨的丈夫原谅。再有,这类女性确有风度,确会耍风流,有极好的应酬功夫。但她们缺少真切的感情交流。一言一行,都有‘笑不露齿、怒不高声“的框订。笑,只不过笑给人家看的;哭,却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朋友呢?结了婚后很难接识到新的朋友。在一道操操麻将,结结绒线,看看电影,听听绍兴戏,谈谈山海经的人倒是有的,不过都是打发自己生命的陪伴罢了。这群女性们知书达理,能领略琴棋书画,却不多自己的才学,不具备本人的思想锋芒。有的小姐,即使曾经光彩照人,捧为校花。只要一踏进淑女的怪圈,无需多久,便成了明日黄花,留下的只是无可奈何的哀叹。张爱玲、苏青等旷世才女,辉煌鼎盛时期不过两到三年,原因要复杂得多,但都与她们的婚姻状况有关。
所以,在对淑女的认可上,市俗订立的标准就显得有几分怪异。譬如,国母宋庆龄女士,其母是上海老祖宗徐光启的后裔,她本人在上海出身、成长。到老话语中仍带有浓厚的乡音。按理说,不管从哪个角度,夫人应为所谓淑女的当之无愧的领袖。然而,上海人不敢提这个。夫人拥有太深切的喜,太深切的悲,对社会有太杰出的贡献,对儿童有太博大的情怀。她们实在承受不了她。同样,对于蒋夫人宋美龄,人们也不可能将她规纳在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否可作这么一个设想。那一位三十年代混迹上海的明星蓝苹小姐,既会“嗲”,又会“作”,三缸水可以搞得六缸浑。弄得男人要死要活的。趟若她后来没有被放出来,祸国殃民,最终被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她能不能挤身于淑女之列呢?你去问问看,我想,上海人又要撇嘴摇头了:“不要触人酶头了,伊算啥末是。”
记不得是程乃珊还是陈丹燕说过的,上海淑女的最大特点是:中庸而别致。在我看来,倒讲得蛮在点子上。
时代
一九四九年五月,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上海被解放。妇女的命运出现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一小部分人走了,去台湾,去香港,甚至还有远度重洋,另处落脚的。但大部分人,依然留在本土,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不管是走是留,均为“随从夫君”。老牌淑女的时代也就此结束。留守的女子们,有了她们的新称号----家庭妇女。在弄堂里,互相见了面,都称呼为“某大姐”。一个个,非常迅速又非常自然地收敛了以往的光艳,脱去了旗袍,穿起女式列宁装来了。再后来,一个个,走出了家门,到社会上谋求职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家中开始发生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为摆脱“家庭妇女”的落后名声。到底都是有文化的,学校里学的没有白白浪费,有的到医院作药剂士,护士,有的当了写字间的秘书,还有的,被分配到小学校当代课老师,踩著风琴的蹋脚板,带领孩子们唱:“我有一双万能的手,万能的手。样样事情都会做,都会做。”
妇女的解放,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件好事。然而,一个巨硕的然而紧紧跟在了后面。鸟儿飞出了笼子,迎接她们的却是无情的疾风暴雨。接下来三十几年的生活渐渐地变得疙里疙瘩了。新社会,社会风气和文化观念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她们要买帐,要承认落后,要改造,要靠拢领导,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对此,她们并不在行,但不得不学起来。有人不惜下了档次,唯唯若若,跟着戳壁脚,搬弄是非。不然的话,就连她们的亲生儿女都看她们不起,“跟你们划清界限”
是她们最怕听到的话,听了心要碎。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她们的男人们都成了特务,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被打翻在地,再蹋上一只脚。女人呢?圣经上说,女人有罪是因为偷吃了依甸园的苹果,这些与夏娃同样简单的女子,甚至还没有那样“不良”或“不从”的念头呢。可是罪名是少不了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身攻击和侮辱也因此大显身手,其中最耳濡目染的是“化作美女的毒蛇”。话是从毛主席语录来的,这一处倒与圣经一脉相承。蛇的本质是引诱,男人变坏,女人是祸首。既然罪名这般定了,当然地成为了革命对象。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而“毒蛇”们的招架能力又极其单薄,甚至要辩解,腿都会抖,舌头会打结。她们只能认了。一场革命,革得她们莫名其妙,革得她们面目全非,革得她们做梦都不敢做她们的“那个失去了的天堂”。《上海生死录》的作者郑义女士,在被逼到绝壁时,只剩下一丝希望,她要比毛主席活得长,只有这样,她才能翻身。这是一位聪明绝顶的女性,她熬过来了。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成为了历史。
今日,小资又弥漫著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据说,在上海的舞厅里,偶尔还会碰到屈指可数的几个老克勒,自以为是又自得其乐地带着女孩子蓬嚓嚓;在公园的英语角,也是这几个人,自说自话又自鸣得意地纠正年轻学生不够“克勒”的英语发音。这些人的年龄,怎么说,都在七十五岁以上,但全是男人。美女们呢?基本上都隐没了。女人的寿命可以比男人长,但她们展现于社会所受到的袢索,比男人多的多。况且,女人对世事的参与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热情。花样年华早已不在,留恋带来的只有伤感。何必不安分,何必要“作”,受人耻笑呢。她们又回到了她们的“笼子”,轻轻地掩了门。窗外有月亮的时候,看著月亮,隔著几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没有月亮的时候,她们感觉恍惚进到了坟墓,她们在静静地等候……
现在,市面上今所宣传的时髦外婆,实际辈份比老牌淑女要低,其代表人物为退休的上海人艺演员周谅量,她曾在黄佐临导演的影片《黄浦江的故事》里,出任女主角。很美,演技也有份量。与她同时代且出名的有祝希娟,曹雷,严丽秋等人。在解放时,她们还未到“杨家有女初长成”的年龄,在解放后受的高等教育,在新社会成长,比起上一代,她们要从容得多了,起码,她们不会只是抵挡。她们的苦恼是她们的青春年华丢失得太没有名堂了,也不甘心就这么老去,她们拾起了时髦。
淑女的隐没是极其自然的社会现象,找不回来的。近几年,市面上又可以见到一些三四十年代的月份牌,阴丹士林布的商标纸,双妹牌爽身粉的罐头,说是古董,又不算古董,你可以从那儿看到她们的倩影,千篇一律的细细的腰,甜蜜蜜的笑,眼泡都是肉鼓鼓的,阮玲玉的模式。“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
又全然不是这回事!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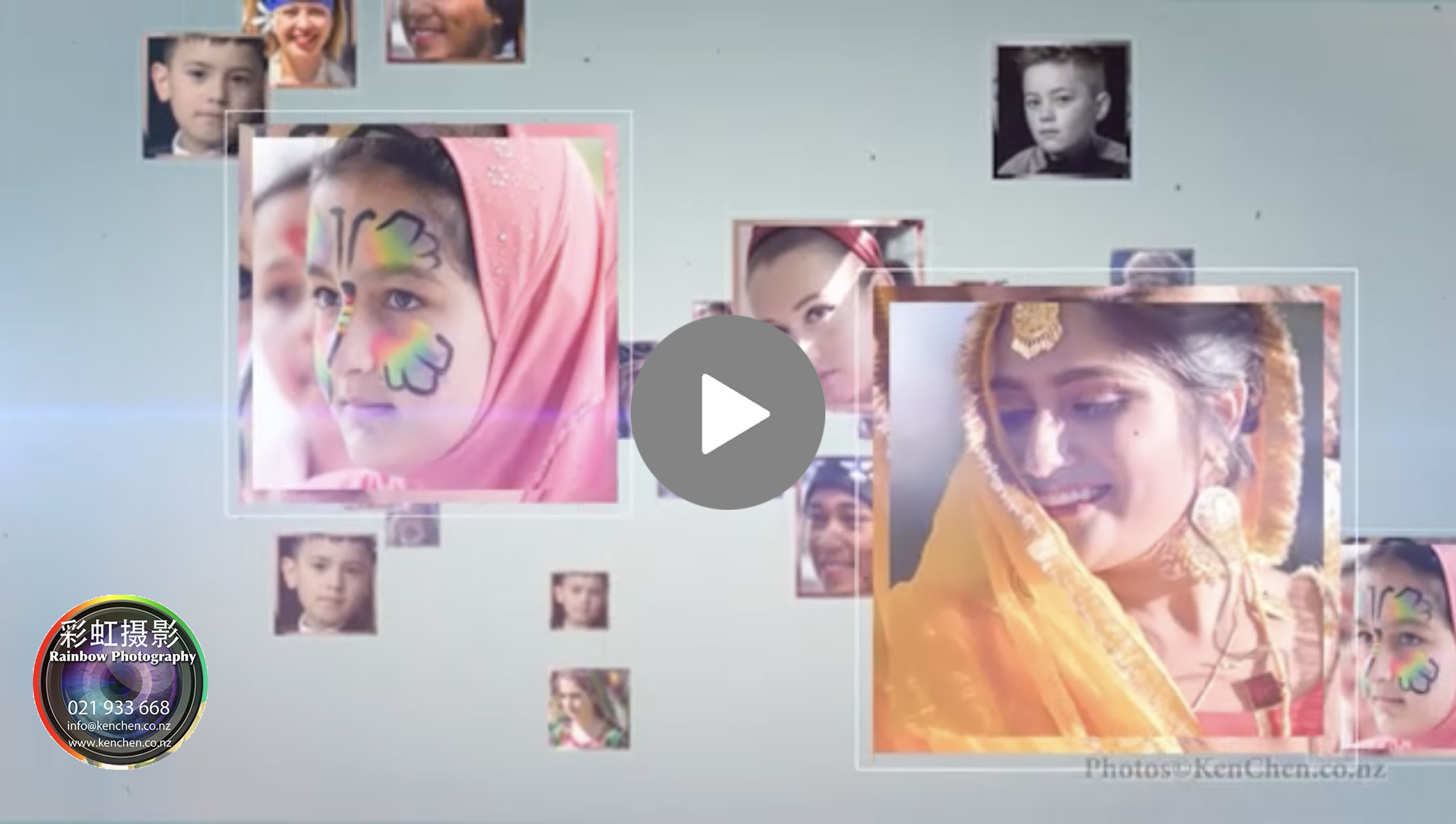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