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读者文摘
永远的雨
作者: 梁琴 人气: 日期: 2003/11/13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唱歌/在她慈蔼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首难忘的歌曲/我的辛酸的眼泪/点点流在我这憔翠的脸上。
——德沃夏克
十年了。整整十年。不敢喊“母亲”。
不敢碰触这个内主的创口。一碰,就流血。心便一撕一撕地裂。
十年了。带血的心呻吟了十年。
每逢端阳来临,家家户户插艾条,酒雄黄,架起大铁锅煮粽子,粽叶的清香,更勾起了一阵阵哀痛。
常常是午夜梦回,泪流满面……
明明才拉着母亲的手,倚着母亲软软的身子,嗅着母亲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一睁眼,便是阴阳陌路,生死两茫茫……
母亲,你走得那么遽然,那么匆忙,连一句话也不曾留下。连小女儿大学毕业都等不及了……
要来的,躲也躲不掉。莫非这是定数?
记得二十岁以前,在我下放的抚河乡下,有个远近闻名的算命瞎子,曾预测我,二十八岁时,家庭有重大的变故。
当时的我,听瞎子这么一说,悚然一惊,然而毕竟年轻,想着遥遥十来年以后的事,并没有往心里去。当时焦虑的只是眼下如何从农村调回省城。
不幸的是,瞎子的预言竟应验了。正是那一年,我二十八岁。
十年前,那个不堪回首的端阳节。
端阳后的第五天,一大清早,当一脸苍白的小妹,抖着发青的嘴唇,哭着捶打我的门,说母亲病得好厉害,不得了。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头天晚上,我们还在家里跟母亲一块看电视,一块聊天,看到晚上九点多钟,天上飘起了毛毛细雨,母亲催促我们走。离家的时候,母亲把我们送出家门,还是好端端的呀。
小妹哭着跑去通知三哥了。先生直接赶往医院找熟悉的医生。我捂着肚子,拼命往家里赶。其时,我刚施行过阑尾手术,还是母亲提前把我接回家过节的。母亲以为,我们家的人是不作兴的医院过节的。
我用手按住伤口,伛着腰,一路祈祷:“主啊,保祐我母”,“主啊,仁慈万能的主,保祐我母”。
待我跌跌撞撞赶回家,远远看见家门口那棵老樟树下,围了一大伙人,我就知道,出大事了。双腿发软,怎么也走不动,心口刀口剧烈地绞痛起来……
母亲的猝死,一下子把遥远而神秘的“生”与“死”的界线,突然拉得这么近,逼视在眼前。
两度昏厥在母亲床头的小妹,醒来哭诉道,怪不得前些日子,她在学校梦见下大雪,很厚一厚雪,覆盖了屋顶……
白的花瓣,绵绵婉转地飘酒、旋落;
白雪,覆盖了一切,生命从此缄口不语……
浑浑噩噩的我们,死神逼进了门坎,竟然毫无察觉,这无边的大雪,便是下在我们心头的霜呵,便是我们披纱的预兆。
母亲撒手西归。支撑我们家四十年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全家人陷入了极度的悲痛……
从此,一切,再无言语。
感情也因霜冻而冰封住了。
大约有两年时光,神情木木的我,像穿了一件盔甲,把自己紧紧裹起来,不跟什么人交往,不再提“母亲”二字……
二十八年来,进门出门,总喜欢老远就喊一声“母亲”的我,有几次脱口而出,一阵惊悸,便被痛苦的感情所咬啮。
又一次失声/失声唤母亲/没有回音/没有回音/只有父亲混浊的泪水/只有姊姊慌乱的眼神。镜框中的母亲呵/你为什么不出声!
这首《清明泪》,哭出了我的一颗滴血的心。
大年初一清早,我和三哥也不管哪家的规矩,冒了严寒,骑上单车跑十多里路,踩着留有残雪的泥泞小径,攀住棘草枯枝,来到公墓,陪伴寂寞的母亲。
不尽的思念,捻成三根细香,袅袅向母亲倾诉……
盘腿静坐在母亲的墓前,默默祷告。一颗疲惫的心感到从未有过的宁静与淡泊。远处山脚下,不时响起劈哩啪啦的爆竹声。
时间在恒静中流逝。
坐在这寂寥的山头,听着隐隐传来的新年的爆竹声响,思索着母亲耗尽的一生,过年的心境一丝一毫都不复存在,一切恍若隔世……
如烟的往事,随着流动的山风,渐渐淹上来……
一个沉沉欲坠的夜,黑雾弥漫。
迷迷蒙蒙的信号灯,在远处闪烁。铁路长长,紧紧攥住母亲的手,沿着铁轨,吃力地抬脚,跨过一根根枕木。
四周黑黝黝的,不敢回头。紧紧贴着母亲,生怕背后突然伸过来一只手,一把把我捉走。
五岁的我,跟了母亲去铁路幼儿园上夜班。带孩子上班,是要被院长严厉训斥的。母亲只能在当夜班时,偷偷带我去一两次。
半夜时分,火车的长鸣,惊醒了我,只听咣当一声,火车停下了。我睁开眼,一眼看见母亲就着昏黯的灯光,有一针没一针地绱袜底。火车咣当停下,而拿在母亲手里的针便开始迟疑,她抬起头凝着窗外,忽然轻轻地叹息了一声,重又低下头绱袜底。
午夜时分,母亲轻轻的一声叹息,使我童蒙的心,初次领略了人世间薄薄的苍凉。
大约在我三岁的时候,一张下放的通知,不期落到我父亲的头上。
虽然父亲不曾戴什么帽子,然而下放是没有价钱可讲的。原先说好去垦殖场三年的。三年之后,自觉劳动改造得很彻底的父亲,夹着农场的奖状,兴冲冲跑回城里,找到原单位,好些人却佯装不认识他,原先答应他三年返城的人事干部,也突然变了脸,矢口否认说过的话。天真的父亲,受到如此蒙骗和打击,精神一下子萎顿了。
整整二十二年,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个二十二年?直到退休,我倍受煎熬的父亲,挟着一只破箱子,一只散了箍的水桶,一顶千疮百孔的罗纱蚊帐,顶着满头的白发,颤颤巍巍回到城里。
二十二年,我的历尽磨难的母亲,领着八个相差一两岁的孩子,独立门户。
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这唯一的生活来源,实在填不满十来张嘴,母亲只得四处托人找工作。
母亲这一生到底干过多少行,谁说得清呢?
新华书店、铁路医院、铁路幼儿园……家的拖累,母亲辞掉了一个又一个工作。
一个雨夜,母亲当夜班。孩子们玩疯了心,玩得忘了拴门,大门虚掩着,一个个东倒西歪睡得好死,连人抬走了都不晓得。
轻易得手的贼,毫不留情,将我们家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全洗劫一空。
下夜班归来的母亲,望着满地凌乱的衣物,望着撬开的老皮箱,一下跌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她摸摸受了惊吓的我和三姐,决然对大姐说,只苦了你们。今天,我就去辞职。
母亲说的憾人的冷静。
为了贴补家用,辞去了正式工作的母亲,不得不去找一些零星活干。冬天包棉花,夏天去废品仓库锉橡胶。实在没有活干,就取下一扇门板,熬米汤打布壳,一层一层的布壳,打得厚厚的做鞋帮、鞋垫。一家大小四季的穿戴,全靠母亲一双手。
终年穿一件洗得泛白的阴丹士林布大襟褂,头上粘着絮花,身上散发橡胶味的母亲,从她身上,再也看不出当年富家大小姐的痕迹了。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母亲迫不得已,狠狠心,让十四岁的大姐冒充十六岁,去邮局报名当学徒。无奈大姐长得又瘦又矮,十四岁的人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小,怎么充大呢?
焦虑的母亲突然有了主意,前些日子有个亲戚托她把几双自己不穿的皮鞋卖掉,何不先借一双高跟鞋,让女儿垫高些,报了名再说。
大姐穿着那双借来的里面塞了棉花的红高跟鞋,高高兴兴去报名。
父亲从农场回来探亲,每次总要背一小袋山货,背得最多的红薯根根,那是队里刨过的地,父亲再刨一遍的收获。
即便是一小袋红薯根,也给贫寒的家带来了生气与快活。一家大小,围坐在火盆边烤红薯,喷香的炭火味,充溢了老屋。
吃完了红薯,父亲也该走了。离家的时候,父亲老是磨磨蹭蹭,一手揽着三姐,一手抱起我,舍不得走。每次都是母亲硬起心肠,一遍遍催促父亲,快些走,车要开了。就这样,父亲还是误了许多次长途班车。
误了车的父亲,背着包,一脸歉疚地推开家门,母亲见了,慌忙躲进厨房,眼泪扑簌簌往下流。
母亲何尝舍得父亲走呢?只不过一趟车票,就是一个孩子半个月的伙食呵。
在这凄清的墓地,三哥打禅般坐着,一连几个小时,连香烟也没抽一根。平时烟抽得很凶的三哥,是不是怕尘世的东西污染了母亲洁净的灵魂居所呢?
“当深重的生活担子,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轻轻地呼唤:‘妈妈,妈妈’,重又获得了生活的勇气,我又继续挑着担子往前走了……”
这是十九岁的三哥,从躺上给乡下的我写了一封信。三哥属老三届初中生,分在远离家乡的一条内河驳船上。
“没有书,没有报,也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只有河水无声无息地静静流淌。晚上,师傅们玩牌去了,我就着一盏如豆的油灯,翻开书本。当我一想到,我不只是一个人,我是属于我们这个亲爱的大家庭的,我就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是什么支撑三哥在柘寂单调的船上生活中,没有沉沦,没有变成因空虚而结伴上岸寻衅,以打架为乐事,以粗蛮称雄的浪荡船民,而是坚执于自己的一份追求,伴着一盏孤灯,自学完了全部的高中课程,成为高考中的佼佼者。
正是母亲,母亲贫困不能移的坚韧,母亲巨大的人格力量的感召。
六十年代初,城市居民按人头供应蔬菜,每人二两。每天清晨三四点钟,母亲把睡在堂屋的三哥叫醒去菜场排队。
从小懂事的三哥,很能体贴母亲的艰辛,即便刮风下雪,也从不让母亲多操一份心,只要母亲里屋的灯一亮,三哥便一轱辘从被窝里爬出来,套件薄绒衣,穿两条单裤,光脚塞进破球鞋里。取过头天晚上母亲搁在床头边的供应卡,抓起门边的菜蓝子,拉开门栓,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
岁月流逝,却冲不淡往事的追忆。每每说起三哥小时候半夜爬起来买菜,母亲总是感慨唏嘘。
熬过了担惊受怕的“文革”,母亲终于盼到了儿女参加工作的那一天。
前脚跟后脚,几乎在同一天,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离开家门,最远的离家上千里。再过一个月,也轮到我下乡了。
热热闹闹的家,一下子冷清下来。
记得哥哥姐姐走的那一天,母亲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半侧着身子坐在床沿,默默饮泣……
又是另一番牵肠挂肚的操心。
默默饮泣的母亲的背影,总让我联想起珂勒惠支的一副木刻《牺牲》。
母亲过后很长一段日子,只要一拐进西大街,一闻到老街上古樟的清香,就仿佛闻见了母亲身上熟悉的气息。一跨进家门,就被一种幻觉所迷惑:母亲刚放下满篮菜,放下一锅豆腐,倚着门框,微微喘息;母亲就站在水池边挽了袖子洗衣服,在天井里拣菜,在厨房里又洗又抹……
仅仅数秒钟,幻像消失了……
母亲去世的头一天,我们还在家吞食母亲名扬一条街的卤牛肉。炒菜的时候,母亲招我进厨房,让我在一旁看着,我觉得好生奇怪,婚后三年,我一直不肯背饭锅,不肯下厨房的,母亲今天急着教我炒菜干吗?
离家的时候,母亲追出门外,喊住我,把一口新铝锅和两把刷锅的竹刷子,硬塞到我手里,边塞边说,你也要学会炒菜,总不能跟我一辈子……
毫无预兆的我,不经意地对母亲笑笑:“妈,急什么,现在还早呢,再过两年,等我毕业了,就来跟你学炒菜,到时我也露一手,让你尝尝。”
做梦也没想到,一夜工夫,母亲竟忍心抛下我们,径自走了……
母亲走的时候,仅仅五十八岁。
母亲,告诉我,从来不曾教我烹调的你,为什么突然间教我炒菜,还急急追出门来送我一口炒菜锅?
母亲呵,是不是潜意识里,你已经有了某种预感,来不及了,一切都来不及了……
一颗仁慈的爱心,是永远不死的。
在冥冥中佑护着她的儿女,她的亲人……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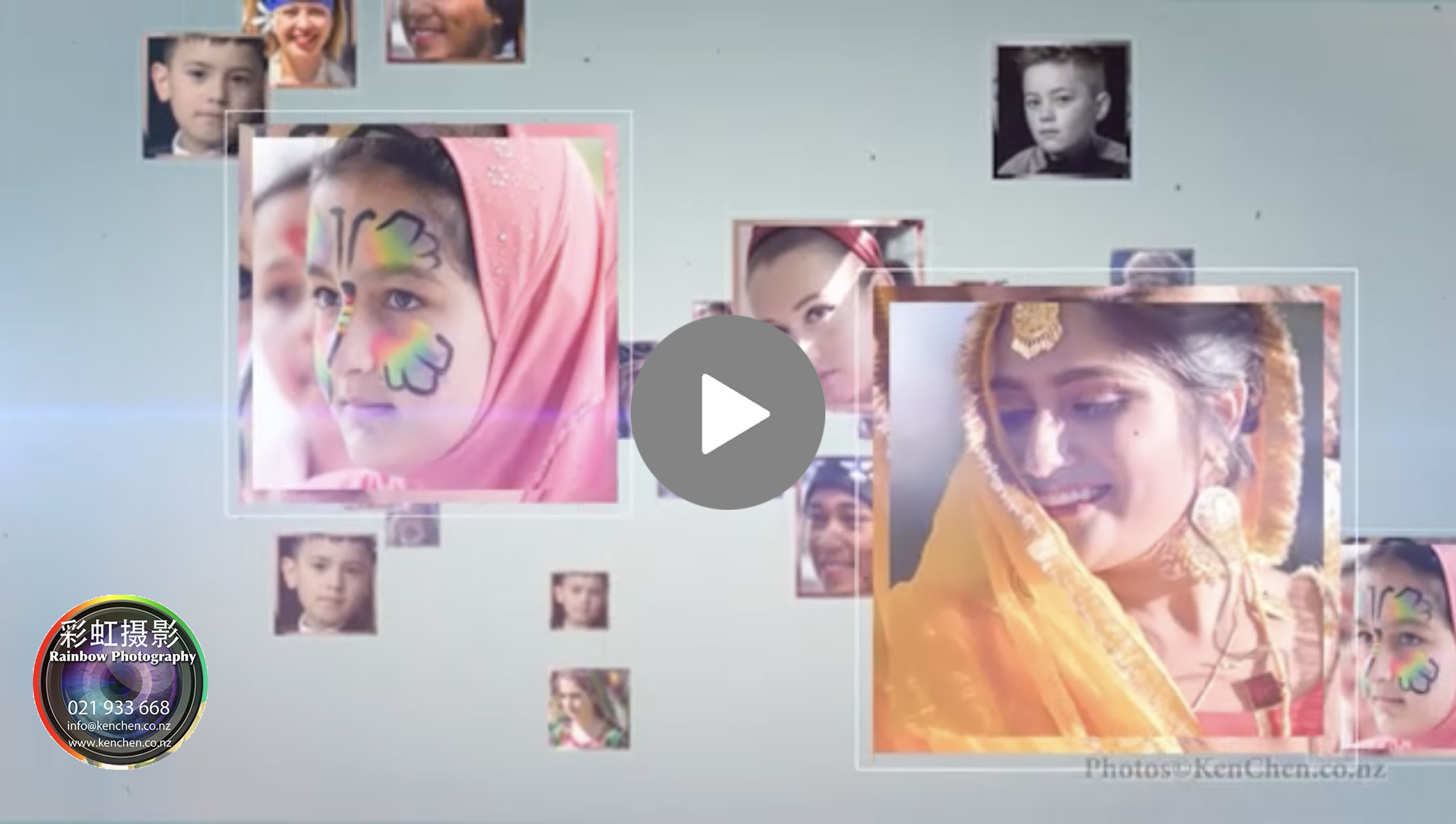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