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长篇连载
悠闲颂 - 怎样才能自由和幸福(2)
作者: (英)罗素 人气: 日期: 2004/10/23 3:39:33 如果我们的生活更幸福一些的活,那么我们不会急于打仗了。我认为,在你们可能称之为“生存意志”的现代社会中看到这一奇怪的弱点是一件相当令人吃惊的事情。有“工作意志”,但没有“生存意志”;你们不会感到大规模的毁灭前景是令人无法忍受的;你们不会感觉到人们为了消除战争的威胁而不惜牺牲金钱和权力;他们并不想真的消灭战争。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为了那无聊的战争事业和无聊的可能的胜利而去牺牲生命。健康和幸福(鼓掌)。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具有集体性而很少个人性。我们,就象我们现在这样,被人类文明的机械模型塑造得越来越彼此相似。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受到大众性情感所左右,而个体性情感的作用则越来越少。在这种意义上,个人作出了某种牺牲。个人牺牲的那部分生活并非他极度喜爱的生活。
我们想像我们需要各种各样东西,诸如权力和财富,这并非幸福之源。你将觉得幸福的真正源泉在《新约·四福音书》中已有了确切地描写。我说的是刚才我所引用的关于不要考虑明天的事情的那番话。如果你有一个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孩子,如果你有任何一件你真正关心的事情,那么这些便是你生命意义之源,这样你们便能团结大量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们。但是如果你以国家为重——“这就是我,我是国家的一员,我希望我的国家富强”——那么你就在破坏个性。你也变得暴虐,因为国家是否强大取决于对人民的统治和是否设法去统治邻国。
个性是最重要的。可能你会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说这种话非常奇怪。我相信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必须交付于社会主义组织。但我相信个性重要是因为我认为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最不重要。只要你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维持生活,那么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由于存在可怕的贫穷,以致于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但现在通过技术性生产,我们完全可以消灭贫困和解决人们流离失所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十足的笨蛋(笑声和掌声入当你想像你将有一个消灭了贫困的世界,你将会明白物质利益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必定会迁入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一天多工作一小时每个成员就多一辆汽车的话。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精神产品更为重要,精神产品比共同体中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价值。共同体将给你分配日常食物和布置日常任务。在你闲暇之余,你能从事其他工作,只要你喜欢你可以去踢足球、看电影或做诸如此类事情。
人们有时间我:你怎么能保证人们会利用好他们的闲暇时间?我不想作这个保证。当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你们依然受不适当的道德的支配,受集体向个人施加过多压力的思维定势的支配。只要闲暇时间没有被用来对他人造成损害,那都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精神世界我们需要个人主义。只是在物质世界,我们才需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人而现在,在精神世界,我们有“社会主义”,在物质世界(领域)我们却是个人主义。(笑声和掌声)
你们将思考什么和你们如何驾驭自己的情感,这被认为是政府应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们是否有足够的东西吃则不是政府的事情——在这里,神圣的自由原则流行起来了。不过它正好被置于错误的位置。我和你们谈的实际上也就是所有伟大宗教领袖曾说过的话即人们的灵魂是一个重要的东西。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最伟大的事情。它就是你自身的灵魂,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理解和你自己的认同感;只要你有足够的东西来维持生活,那些外表的生活装饰则不重要。我们之所以不懂得这一简单真理是因为竞争意识已深入我们的骨髓里了。
我一直和你们谈得相当随便,但我所指的都是极其生动的事情,是一种真正的解放——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获得解放,这样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不再担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好象不再重要。任何人,无论男人或女人,其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激情,一旦拥有了它,你就不会再在乎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琐事。你们就能这样生活——自由地、开朗地生活!你们将发现,一旦你们不再有“伯”字,你就能与他人更亲密地相处,你们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友谊的乐趣。整个世界因而会更有趣、更生动,因而也更有价值。无论曾经体验过这种激情的人是谁,他都知道它比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的东西要好得多。这是一个古老的秘密——所有的老师都教过但牧师们却将它忘记了;它就是与这个世界密切联系的秘密,而不要筑一道坚硬的自我之墙以致你看不到墙以外的精彩世界。道德家们总以为“我是多么道德啊!”,实际上他与其它人一样也是个自我主义者。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中,你无法获得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它只能存在于已抛弃了恐惧的世界,因为忍受一点伤害是值得的——它来自于对有比避免伤害更有利的事情这一事实的认识——这就是一种人类与世界的紧密融洽关系;一种炽烈的爱,也就是一种灼热的、强烈的象是个人的然而却也是属于大众的情感。如果你能获得这一切,你就懂得了幸福生活的真谛。三.如果我们想幸免于这个黑暗时代
我们有很多理由去担心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整个世界的话——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经历一个巨大的悲哀、不幸与痛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如果我们不谨慎地牢记它们,我们现在正试图保存的东西将随着辛酸、贫穷与混乱而被人遗忘。勇气。希望与毫不动摇的信仰,如果我们试图从这一黑暗时代脱身出来且精神不致受伤的话,就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在真正的危险降临我们之前,很有必要去集中我们的思想、调整我们的希望,并把我们的理想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心灵深处。
这种威胁到西方世界的灾难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罗马帝国的衰败就是其一,在那时就象在现在一样,各种不同的失望情绪、逃跑情绪和顽固的信仰,在时代的精英人物的著作中不时地得到反映。基督教会就是从这一危机中生长出来的,并且最终成为了新的文明的核心。许多异教徒,其思想是高尚的,其抱负也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们缺乏推动力量。
普罗提诺这位新相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是这一时期是杰出的异教徙。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希望在世界事务中起一定作用,并因此伴随罗马帝王远征波斯,但是罗马士兵杀害了这位皇帝并决定返回家乡。普罗提诺使尽了浑身解数,方才平安到家,从此决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他躲进书斋,陷入了沉思,并且写出了一部部美文华章。在这些书中,他赞美这永恒的世界和这世界的静静思索。这种哲学,不管其本身如何值得称赞,都不能给帝国遭受的苦痛提供医治的良方。
我认为,普罗提诺在他提醒人们注意思考永恒世办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然而在把这种思考当作美好生活的基本成份这一点上却是错误的。沉思,如果它要变得完整和有意义的话,必须与实践连结起来。它必须激起行动,使实际的政治目标受人尊崇。当它被深藏干隐居地的时候,它仅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
代表了罗马文明的最后繁荣的波爱修,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终生献身于公众管理事业,企图教化哥特人的一位国王,结果招致了灾难,被叛死刑。在狱中,他编辑修订了他的伟大著作:《哲学的慰藉人在该书中,他以一种奇迹般的乐观的理性态度——就仿佛他仍是一位强有力的执政官似的——表明了自己的沉思的快乐,对美好世界的欣喜以及对人类的希望,因为人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未将他遗弃。在整个黑暗时期,他的著作被人传诵着,并且一直流传到古代世界的最终纯粹化了的遗产——一个更为幸福的时代。
我们时代的圣人们有着同样如此行动的义务。巩固那些使我们的时代变得伟大的成就、希望和理想,乃是他们对后代的不可推辞的责任——率直诚恳地研究它们,以使它们象黑暗中的灯塔一样,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人类生活的两个极为木同的概念正在互相斗争,以便夺取对这个世界的统治权。在西方我们看到个体生活对于人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伟大的社会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获得各自的幸福、自由、创造性。我们从不认为个体应该相类似。我们相信,社会的一曲交响乐,各种不同的演员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各自拥有不同的表演器具,并且其和谐来自于一种有意识的共同目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自豪之处。他应该具有他自己的良知和目的,除非已经显示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性后果,否则他便应该自由地发展这些良知,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极为重视消除痛苦和贫困,也重视知识的增长以及美和艺术的创造。对于我们来说,政府只是一种便利性工具,而非崇拜的对象。
俄国政府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目的概念。个体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掉的。只有政府才是重要的,才是神圣的,其自身具有一种利益,这种利益并非由个体利益所组成。这一看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它从根本上是与基督教伦理相对立的,在西方,这种基督教伦理不仅被基督教徒所接受,也被自由思想家们所接受。在苏联的社会中,人的尊严等于零。
人们常常认为,在那个体现了政府的伟大性的精神似的存在物面前屈膝下跪、卑躬屈节,是正确而恰当的。当某人背叛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并且作为对朋友的瞬间轻率行为的惩罚,他还使他陷入一种对西伯利亚集中营的神秘恐惧之中时;当一位学生,由于他的教师的灌输教导,使他的父母被判死刑时;当一个有着超人的勇气,并同邪恶势力作过英勇斗争的人,被严刑拷打、被无理审讯,并且最终木得不无奈何地承认自己触犯过反对当局的莫洛克式①的权力的罪行时,不管是背叛还是坦白都未能给作恶者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羞愧,难道会是因为他未曾眼膺于他自己的神性?
正是这一概念,我们必须与之斗争。在我看来,并且在大多数赞赏西方立场的人看来,这一概念,如果得以流布的话,将会把生活赋予的一切价值全部清除,除了大难大堆的卑屈动物之外,什么也没留下。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大的或者深刻的理由说我们不必与之斗争。但是,如果我们要想赢得胜利——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人的心中和他的持有的传统中——我们就必须先擦亮自己的眼睛,纯洁自己的心灵,弄清楚我们的价值所在,同时,我们必须象波爱修那样,增强自己应对灾难性威胁的勇气。
当俄国过分低估个体的价值时,在我们西方,却有一些过分提高独立个人的独立性的人。任何人的自我都不能被禁闭于花岗岩墙之中;其界限应该是半透明的。智慧的首要步骤,正如在道德中一样,乃是尽可能地打开自我之窗口。许多人发现,把他们的孩子包括进他们的意愿中,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在稍许弱小些的程度上,他们还包括了自己的朋友,在危急的时刻甚至也包括了自己的国家。很多人觉得,损害他们国家的东西也损害了他们。在1940年,我知道许多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却遭受了亡国之痛的法国人,其痛苦之状宛苦遭受了截肢之痛。但这还没有将我们的同情心增强到足够容纳我们自己国家的程度。如果世界永远充满了和平,我们就有必要学会以一种与我们现在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的同样的同情态度,容纳进我们全部的人类。并且,如果我们想在艰难时刻保持平静与理智,我们的头脑要是能包含进过去与未来的所有时代,这将是极有助益的。
对于我们的价值概念来说,再也没有比思考一下人类从他的蒙昧而艰难的起步逐渐进化到现在的优越地位,更令人清醒明白了。人当他第一次出现时,乃是一个数目稀少而被追猎的动物,他不如鹿儿轻巧,不如猴儿敏捷,无法抗拒野兽的侵袭,没有抗拒雨水和寒冷的温暖皮毛,没有稳定的食物以供采集;他没有武器,没有驯兽,没有农业。
他唯一拥有的优势——智力——给了他安全。他学会了使用火、弓箭、语言、驯兽以及最终才学会的农业。他学会了在团体中的合作,学会了建造巨大的宫殿和金字塔,学会了开垦四方的世界,并且最终学会了对付疾病与贫穷。他研究星象,发明了几何学,并且学会了以机器代替必要的体力劳动。其中许多重大进步乃是最近的事,并且仍然只限于西方国家。
过去的日子里,许多孩子夭折在摇篮里,成年人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并且在每个国家,人口的绝大部分还是忍受着可伯的贫困的折磨。现在,某些国家已经成功地保护住了绝大部分婴儿的生命,极大地降低了成年人的死亡率,并且几乎消除了可怕的贫困。其他国家,即那些疾病和贫困猖狐的国家,通过采用同样的方法,可望达到同样的发达水平。因而,人类还有新的希望。
除非邪恶现象的根源得到理解,否则我们是别指望认识到这种希望的。但我仍必须强调这一希望。现代人是他又己的命运之神。他之所以遭受这些遭受,是因为他愚蠢或怯懦,而不是因为这是天命注定的。人只有抓住了近在手边的武器,他才可能获得幸福。
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人,面对共产主义的恶意批评,显得过于谦卑、过于保守。自从生命出现以来,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进化机制就包含了残酷的折磨、无止境的生存抗争。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最终的饥饿死亡。这是动物王国的天然法则,并且直到最近的几个世纪里,也是人类的天然法则。如今,某些国家最终发现了摆脱可怕的贫困的途径:发现了防止末成年人死亡所带来的痛苦、忧伤和无谓的浪费的途径;还发现了用智慧和爱心代替自然的盲目无情的途径。
已经有了这些发现的国家是人类未来的托管人。他们必须充满对新生活方式的勇气,必须使自己保持清醒,不被半开化文明的口号,搞得茫然无措、神情紧张。我们有权力希望,这全是理性的,能够被详细证明的,和能够用统计数据加以陈述的。如果我们让自己由于那些非理性的梦魔丧失了这些希望,那就是对人类的背叛。
如果我们前面是艰难岁月,当这岁月久驻不走,我们必须牢记人类的漫长进化史,这段历史是混乱退步交错的历史,但它的结果总是重新恢复进步的运动。斯宾诺莎是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曾经严格遵守他的智慧的教学生活,主张人应该把过去的事情看作是“永恒的一个方面”。那些懂得如此看待的人将会发现,痛苦的现在比起不如此看待来要容易忍受得多。他们将把它看作是过眼烟云——一个已被解开的结,一条已被跨越的河。自己弄伤了自己的孩子哭得眼泪滂论,似乎世界除了悲伤再也没有其它什么,这是因为他的心灵仅仅限于当前。从斯宾诺莎那儿学得了智慧的人能够把哪怕是不幸的时刻也看作是人类历程的短暂起伏。并且人类本身,从他的蒙昧起源到它的未知结局,也只木过是宇宙历程的短暂插曲。
我们对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并不知晓,但要说宇宙包含的东西,再也没什么比我们的好,这却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随着智慧的增长,我们的思想获得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更为宽广的视野。婴儿以分为单位生活,少年以天为单位生活,本能的成人以年为单位生活。富于历史感的人以世纪为单位生活。斯宾诺莎使得我们既不以分、天、年为单位,也木以世纪为单位,而是以永恒为单位生活。学会了这一方法的人将发现,它驱散了不幸的虚幻因素,阻止了随可怕的灾难而来的疯狂倾向。斯宾诺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仍在向他的房东讲述着风趣的故事。他曾写道:“聪明人考虑死亡比任何东西都少”,并且他一直恪守这一箴言到生命的结束。
我并不是说聪明人应该冷漠无情——恰恰相反,他应该比那尚未摆脱个人焦虑的人更加热爱友情、仁慈和同情。在他与其他人之间他的自我不是一堵墙。他将像佛阳一样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会感到痛苦——比起自我主义者来,这是一种更加宽广和深沉的痛苦——但他不会发现这种痛苦不可忍受。他不会受这种痛苦的驱使以至于创造出一系列舒心宽情的好故事,保证再也不会有其它的不幸发生。他不会丧失冷静和自制能力。正如米尔顿的撒旦,他会说:
灵善守其位,在其中天堂就是地狱,地狱就是天堂
首要的是,他会牢记,每一代人都是后世子孙的精神和道德精华的托管人,这些精华乃是人类世世代代逐渐积累而成的。忘记人类的荣耀是很容易的。当李尔王濒临疯狂边缘时,他遇到了假装痴癫、只穿一条毛毯的艾德加。李尔王当即说教道:“别扭扭捏捏。除了象你这样的贫穷、赤裸以及双脚叉立,人再也没有什么。”
这只是真理的一半,另一半被哈姆雷特说了出来:
“人是一件多么完美的作品!理性是如此崇高!能力是多么无限!行列与行进是多么快速,多么值得羡慕!行动多象天使!智慧正如神灵!”
苏联人卑躬屈膝,不惜背叛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以便延缓一下被屠杀的命运,是很难适合于哈姆雷特的话的,但哈姆雷特的话却适合于他们。这适合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能拓宽自己的心灵、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以及撒播自己的爱心和仁慈。并且只有这样做的人才会最终受人尊敬。东方崇信佛陀,西方崇信基督。他们两人都把爱说成是智慧的谜宫。基督的俗世生活年代与泰伯琉斯帝王是同时的,后者把一生用于残暴和淫逸。泰伯琉斯拥有力量和权力;在他的生活中千千万万的人对他毕恭毕敬。但历史学家们却忘记了他。
即使在有生之年默默无闻,但只要生活得高贵,他就不用担心自己白向世间走一回。从他的生命中放射出某种光辉,这光辉照耀着他的朋友,邻人前进的路程——也许永不熄灭。我发现现在有许多人,总被一种无能的感觉所压抑,并且感到在庞大的现代社会面前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这是错误的。个人,如果他能对人类充满爱心、保持宽广的视野、富于勇气和坚韧,就大有作为。
按照地质年代计算,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出现到现在还只是一瞬间的事,文明从首创到如今也只是眨眼之间的事。虽然有些人危言耸听,但我们的种类很可能不会完全自动消失。人类既然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也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不管他一时遭受些什么,也不管什么样的光彩被遮蔽,他迟早会重新出现,也许在一段时间的精神休眠后变得更加强劲,更加富有活力。宇宙广漠无垠,人类只是它的并不重要的一颗行星上的些微点缀,但我们越认识到自己在宇宙力量面前的短暂和无能,就越能为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震惊。
正是这些可能的人类成就才是我们最终的忠诚所在,并且正是由于这一想法,我们喧嚣的世纪中那些短暂的挫折才变得可以容忍。许多智慧尚待学习,而且如果它们只有通过不幸才能习得,我们就必须以我们最大的坚韧毅力努力去容忍这些不幸。但如果我们马上就能够获得这些智慧,不幸就是不必要的,人类的未来也许就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幸福甜美。四、没有恐惧的生活
曾经使我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一度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恐惧,人类并未从新的科技中得到益处,这些科技,如果被明智地加以运用的话,本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恐惧使人在人类行为的三大领域内变得极不明智,这三大领域就是:对待自然的领域,对待他人的领域,对待自我的领域。在本文中,我希望考察一下如果我们摆脱了古代恐惧的统治,我们的世界如何变得更加美好的各种方式。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开两种恐惧,一是作为一种情感的恐惧;二是作为一种知识的对危险的理性把握。当危险确实存在时,如果对此毫无所知,那将是十分愚蠢的;但是靠恐惧而不是靠理性把握,则很难有效地应付危险的情况。恐惧是我们与动物共有的反应。它是本能的、突然的。有时它起着自我保护的作用,但有时它却起着与此截然相反的作用。没有被恐惧感攫住的人,能够极为明智地发现何种行动能够清除危险。恐惧经常妨碍人们承认他们实际上正在面临着的危险,从而使得他们提不起理智本该提起的警惕。有时,这一情况采取了极为荒唐的形式,例如,对死亡的恐惧有时居然使死者忘了立下遗嘱。明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倒有可能误认为,反对恐惧就意味着反对对真实危险的明确认识。
不同的危险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由于大自然的物理事实的存在,人类不得不屈服于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此程度上人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从我们与他人或者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中也会产生一些妨碍美好生活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由于憎恨或恶意,人们互相之间产生的痛苦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从一种负罪感中,人们也为自己造成了无法逃脱的苦难。由于这一原因,对付不同的罪恶的方法也是极不相同的。
大自然强加给人的限制包括食物的限制、原材料的限制以及死亡的生理事实三个方面。但这些都木是绝对的。通过更多的劳动,人们有可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通过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们可以节约原材料或者利用新的、过去曾被认为毫无用处的材料。死亡可以因治疗和科学的养生术而推迟。但是在这三个方面,虽然我们不能精确地确定限制的界线,限制总还是存在的。再多的药都不会使人长生不老。如果人类连立足的地方都不够,再好的科学都提供不了充足的食物,大自然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这些限制,我们必须科学地加以认识,以便我们在面对它们时,能采取一种导致最少苦难的态度。关于食物问题,解决的方式只能是计划生育。至于原材料问题,答案一半在于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半在于国际性合作,以便防止浪费和保证合理分配。死亡的推迟是医学上的事,但是推迟的意向倒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对此我将在以后再展开讨论。
过去,大自然强加给人的限制常被人以一种迷信的方式加以对待,世上有神灵,也有魔鬼,还有能唤起邪恶精神的巫师;并且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将引来恶劣天气。时至今日,大主教们还认为干旱和洪涝可以通过祈祷去消除。迷信所要求的各种方式往往助长了邪恶势力。在中世纪,当瘟疫流行时,人们却被召集到教堂里作祈祷;这当然为病毒扩散提供了理想的途径。这些邪恶行为,如果它们真能被根除的话,那也只能由科学来根除。在寻找根除的手段时,促使人们承认罪恶与知识的科学态度本身也有一定的两面性。世界上现在依然还有许多罪恶,它们中最可怕的也许就算人口过剩了。由此可知,大部分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从总体上说,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
对他人的恐惧,就我们已知的角度看来,常常是极为顽固的病症,也就是说我们总以为世上有一些人,只要他们做得到,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伤害我们。然而就算这是真的,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靠恐惧来阻止那些对我们有恶意的人伤害我们。如果你曾经豢养过一只狗,而这只狗有着追逐羊群的嗜好,你就会发现,即使它在羊群静安不动时会显得温文尔雅,但只要羊群开始跑向远处,它就再也不能抗拒诱惑。在这方面,我们中的许多人象狗,也有许多人象羊。我曾经看到过一次在一只丹麦种大狗和一只只有三周大的小猫之间的纯粹心理遭遇战。小猫停在老地方,口中发出呼喀呼啃的怒吼,全身毛发直立。那只丹麦种大狗头脑中想的是什么,我并不知道,但它的行动似乎表明他认为小猫有一种超自然的保护力。在一阵作腔作势之后,它把自己的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然后转身溜走。如果你具有这只小猫般的勇气,面对一连串的攻击,你将会有效地保护好自己,否则的话,你将蒙受这种攻击造成的苦难。但是,这种行为常常只是动物才能做到的,而我更加关注那些只有人才能作出的行为。世上许多攻击都是由于恐惧引起的。我们之所以对自己的邻居发怒吼,只因为害怕他攻击我们:他之所以对我们发出怒吼,原因也只不过如此。试图通过友善的表示以免被人攻击,这是并不少见的情况。这也是非抵抗主义学说的真理成份。对于这种学说,如果它采取的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和绝对的形式,那我是不同意的,但它确实包含了相当大的实践智慧成分,虽然大多教的人并不如此认为。我认为,每一个并不显示攻击性意向的人,能够在消除他人具有的一些攻击性意向方面,做一些事情。即使是行为方式的外在准则在这方面也会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一旦非攻击性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性格之中,它的影响就会比它仅仅从传统准则中产生出来所达到的影响大得多。
不管什么时候,一旦日夜担心的危险真的来临,强烈的恐惧笼罩我们时,需要做的往往有两种不同的事情:一种是,造就一种坚毅品格,使得我们能平静地面对可能到来的不幸;另一种是,按照一种能使危险得以消除的方式改良社会制度。例如,这种方式就可以被用于对付贫困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所有竞争的国家中非常普遍,并且很深蒂固。绝大多数看起来无论怎么都是健全的人,却对金钱有着一种完全是非理性的态度。总有那么一些人,虽然他们很愿意开大额支票,却不肯放弃使用散钱付账,而宁愿受到那些还没有闹翻的传者的冷眼。有一类恐惧,即使在大量彻底的成功之后,仍然难以消除。要防止这类恐惧,需要做的往往有三种不同的事情。第一种是纯粹斯多葛式的方法,这种方法劝慰人,要他平静坦然地面对不幸,哪怕不幸真的降临,也不要使它们占去自己过多的心神。另一种方法是告诉他,他很可能不会受到贫穷的威胁;温和一点的话,这可以通过经济学观点来作论证;极端一点的话,则可以通过精神疗法来进行。最后一种方法则是政治性的方法,它通过政治手段去对付整个贫穷问题,使它不再成为一个不幸的问题。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应该追随所有以上这些方法。在确实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斯多葛式的方法也木妨一试,但是,即使一个人有面对不幸的坚强勇气,如果能够避开不幸,那当然更好。很明显,当恐惧达到一种可怕的程度时,它往往产生于那种真实的不幸并不少见的社会里。因而,那种仅与个人有关的方法虽然也能显示出它应有的效用,但却无法代替那种通过政治手段彻底消除罪恶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对勇气抱有如此大的热情,以至于往往为有机会锻炼这种勇气而欣喜莫名。这是荒唐的。你也许会钦佩一个忍受了长期的疾病之痛苦折磨而毫无怨言的人,但如果他能享有更为健康的体魄,这显然好得多。你也许会敬仰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但如果他没有牺牲,事情会好得多,在这一点上,斯多葛派难免会受到责难,因为他们过分看重了忍耐,以至于使得残酷看起来也是一种善,因为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最高的善的东西来说,残酷是达到这种善的必要的手段。人们往往习惯于赞赏穷人们的高度的忍耐力,但这已是在他们获得选举权之前的事了。
在个人生活中,个人在面对社会时往往充满了恐惧,这种现象在英国格外普遍。人们拼命压制自己,不让自己过于草率而受到伤害。他们尽其所能地把感情专注于自我身上。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只要他们无意于自私地欺骗你,他们就会严格地按照你的方式行事。他们死板教条、软弱胆小、消极被动。他们身被一层特制的盔甲,以便把吓坏了的孩子们隐藏起来。结果是,社会交往变得繁琐沉闷,友谊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踪无影,爱情也变成了它本该具有的东西的灰色阴影。人们喜欢引证布朗宁的一段句子:
感谢上帝,是你创造了这难以伺服的家伙
化自诩心灵有两面,一面面对俗世生活
一面向他心爱的女人炫耀。
我并不是一位心理分析专家,但我想,如果我真是的话,我就能讨论一下布朗于的这种感激之情了。他用以面对世俗生活的那一面心灵乃是这样的:他感到他能开辟这块生活的荒原,而用不着害怕受到伤害;在其中没有嘲弄奚落,也没有导致痛苦的知识。其心灵的另一面,即向他心爱的女人炫耀的那一面,包含了全部的虚荣、自负和夸夸其谈,一旦面对同一个俱乐部里的男人时,他就再也不敢炫耀了。后一面同前一面一样,都是恐惧的结果,因为前一面阻止任何新鲜气息进入到他的自我框架中,除非互相吹捧,这心灵是谁也不允许进入其中的。外部世界是苍白黯淡的,内部世界则是固步自封的。这并不是人际关系所应有的状况,人际关系应该是自由的、自发的。虚荣心应该少一点,嫉妒心应该淡一点。固步自封的习惯不仅很容易使自我欺骗暗中滋生,而且,由于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纯粹消极的自我形象的保护上,因而极大地减少了用于好的方面的精力。这种习惯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这就是,它使人更倾心于掩盖起自己的友谊冲动,因为一旦这种冲动被人发觉,就会使他们感到自己非常脆弱。短时的单调沉闷以及长期的思想僵化,就是这种社会性恐惧的统治结果。
我并没有把无恐惧的世界想象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某个方向,它是自由的,而这个方向正是现在所限制的方向。在另一个方向,现在有着自由,却正是它试图加以立法的方向。以后,将有一些法律来调整食物供应和原材料分配。而首要的是,将有一部专门用来阻止战争的法律。我还想,除非在教育的过程中人们注入了某种东西,否则,一个没有过分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当人的属性受到关注时,才会有科学的道德准则存在,这一准则就是:一种试图弄清事实真相,并在弄清事实真相后坦然予以承认的习惯,如今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感伤主义者,他们在发现不利的事实时,仅仅简单地拒绝承认了事。思维的这种习惯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因为不利的事实,在它们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有着更为不利的影响。知识准则即主动承认事实的意愿,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当自然力量确实存在时,对之不予承认当然是极为愚蠢的,而这样的自我评价则更是理智的丧失。
由于物质属性的作用,某些只有教育才能造成的习惯,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不相信一个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会刷牙,确实,一个从小不识害虫为何物的孩子,是不会懂得清洁的重要性的。健康的保持需要物质上的一定的节制,而这种节制,孩子们仅仅通过事后的告诫,是很难懂得的。我认为一定量的节制在教育中是必要的,这木仅仅是为了健康的原因,而且还在于它能造成那些人们对之争议极少的社会行为习惯。我们不会在吃饭时抢走邻居的饭碗,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了不要这样做。在我们长大成熟的很久以前,这种习惯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脑海里,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意识到它。准时吃饭,虽然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但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极大地减少了用在吃饭上的时间和精力。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习惯的养成必须成为早期教育的关键部分。一些现代教育工作者也许给教育带来了更大得多的自由,然而,还有一种自由,也是教育工作应该加以保护的——虽然它现在还未如此实行,这一自由就是我讲的情感自由。保护情感自由的原因有多重:一方面,对情感的过分限制容易使人麻木不仁,并且导致活力的丧失;另一方面,不容许发泄的情感容易变坏,它会寻找一个较之原来被禁止的发泄出口更有害的发泄出口。还有第三种原因,这就是,无论何处,只要一个社会被紧紧地捆绑在传统准则上,许多其实并没有害处的情感也会被认为不可取。因此,我认为,虽然考虑到科学事实,考虑到某些没有了它们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困难的习惯,节制是必要的,但是在教育中,对于情感的节制却是越少越好。首要的是,千万别有这种企图,即引起表达一种很可能是虚假的情感的企图。
过去的教育工作者大相信原罪说了,以至于总认为,孩子们应该被教育成某种与自然状态截然不同的人。这种教育的极端例子,要算圣·奥古斯都关于他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叙述了。拉丁文,他说,他是在母亲的膝下毫无困难地学会的,当然,最后他掌握得很好。希腊文,他是从一位非常严厉的男教师那儿学会的,这位老师动则打人,苛刻之极,结果——他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学好它。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那位男教师教他的方法好,因为——他说——这种方法治好了他的“有害的欢乐”。这一番叙述是教育工作所持观点的再好不过的对立面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看待孩子,应该像一位园艺师看待草木一样,他所做的,就是如何给以适当的土壤和适度的水份,使它们得以成长。如果你的玫瑰花没开放,你不会想到去鞭挞它;而且试图找出在对待它的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错。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成功,你应该象对待玫瑰花那样去对待他。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非一种消极的态度。重要的东西是孩子做了什么,而不是孩子没做什么。并且他们所做的,如果确实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必须是他们自身活力的自发表现。如果你拿定了主意,你可以为孩子们准备一种军事生活,告诉他们在听到命令时,全部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孩子们将会在挫折感中长大,变得发育不全,对世界充满了很深蒂固的愤怒和仇恨——毫无疑问,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被雇来杀人的士兵,这种情感就是十分有用钢;然而,如果他想成为一名和平世界的幸福公民,这种情感就不再是有用的东
我们想像我们需要各种各样东西,诸如权力和财富,这并非幸福之源。你将觉得幸福的真正源泉在《新约·四福音书》中已有了确切地描写。我说的是刚才我所引用的关于不要考虑明天的事情的那番话。如果你有一个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孩子,如果你有任何一件你真正关心的事情,那么这些便是你生命意义之源,这样你们便能团结大量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们。但是如果你以国家为重——“这就是我,我是国家的一员,我希望我的国家富强”——那么你就在破坏个性。你也变得暴虐,因为国家是否强大取决于对人民的统治和是否设法去统治邻国。
个性是最重要的。可能你会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说这种话非常奇怪。我相信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必须交付于社会主义组织。但我相信个性重要是因为我认为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最不重要。只要你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维持生活,那么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由于存在可怕的贫穷,以致于物质利益是最重要的。但现在通过技术性生产,我们完全可以消灭贫困和解决人们流离失所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十足的笨蛋(笑声和掌声入当你想像你将有一个消灭了贫困的世界,你将会明白物质利益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必定会迁入一个社会主义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一天多工作一小时每个成员就多一辆汽车的话。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精神产品更为重要,精神产品比共同体中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价值。共同体将给你分配日常食物和布置日常任务。在你闲暇之余,你能从事其他工作,只要你喜欢你可以去踢足球、看电影或做诸如此类事情。
人们有时间我:你怎么能保证人们会利用好他们的闲暇时间?我不想作这个保证。当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你们依然受不适当的道德的支配,受集体向个人施加过多压力的思维定势的支配。只要闲暇时间没有被用来对他人造成损害,那都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在精神世界我们需要个人主义。只是在物质世界,我们才需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人而现在,在精神世界,我们有“社会主义”,在物质世界(领域)我们却是个人主义。(笑声和掌声)
你们将思考什么和你们如何驾驭自己的情感,这被认为是政府应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你们是否有足够的东西吃则不是政府的事情——在这里,神圣的自由原则流行起来了。不过它正好被置于错误的位置。我和你们谈的实际上也就是所有伟大宗教领袖曾说过的话即人们的灵魂是一个重要的东西。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最伟大的事情。它就是你自身的灵魂,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理解和你自己的认同感;只要你有足够的东西来维持生活,那些外表的生活装饰则不重要。我们之所以不懂得这一简单真理是因为竞争意识已深入我们的骨髓里了。
我一直和你们谈得相当随便,但我所指的都是极其生动的事情,是一种真正的解放——从整个世界、整个宇宙获得解放,这样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不再担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好象不再重要。任何人,无论男人或女人,其灵魂深处都有一种激情,一旦拥有了它,你就不会再在乎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琐事。你们就能这样生活——自由地、开朗地生活!你们将发现,一旦你们不再有“伯”字,你就能与他人更亲密地相处,你们能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友谊的乐趣。整个世界因而会更有趣、更生动,因而也更有价值。无论曾经体验过这种激情的人是谁,他都知道它比通过其它方式得到的东西要好得多。这是一个古老的秘密——所有的老师都教过但牧师们却将它忘记了;它就是与这个世界密切联系的秘密,而不要筑一道坚硬的自我之墙以致你看不到墙以外的精彩世界。道德家们总以为“我是多么道德啊!”,实际上他与其它人一样也是个自我主义者。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中,你无法获得自由和幸福的生活,它只能存在于已抛弃了恐惧的世界,因为忍受一点伤害是值得的——它来自于对有比避免伤害更有利的事情这一事实的认识——这就是一种人类与世界的紧密融洽关系;一种炽烈的爱,也就是一种灼热的、强烈的象是个人的然而却也是属于大众的情感。如果你能获得这一切,你就懂得了幸福生活的真谛。三.如果我们想幸免于这个黑暗时代
我们有很多理由去担心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整个世界的话——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经历一个巨大的悲哀、不幸与痛苦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如果我们不谨慎地牢记它们,我们现在正试图保存的东西将随着辛酸、贫穷与混乱而被人遗忘。勇气。希望与毫不动摇的信仰,如果我们试图从这一黑暗时代脱身出来且精神不致受伤的话,就是非常必要的东西。在真正的危险降临我们之前,很有必要去集中我们的思想、调整我们的希望,并把我们的理想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心灵深处。
这种威胁到西方世界的灾难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罗马帝国的衰败就是其一,在那时就象在现在一样,各种不同的失望情绪、逃跑情绪和顽固的信仰,在时代的精英人物的著作中不时地得到反映。基督教会就是从这一危机中生长出来的,并且最终成为了新的文明的核心。许多异教徒,其思想是高尚的,其抱负也是值得称赞的,然而他们缺乏推动力量。
普罗提诺这位新相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是这一时期是杰出的异教徙。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希望在世界事务中起一定作用,并因此伴随罗马帝王远征波斯,但是罗马士兵杀害了这位皇帝并决定返回家乡。普罗提诺使尽了浑身解数,方才平安到家,从此决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他躲进书斋,陷入了沉思,并且写出了一部部美文华章。在这些书中,他赞美这永恒的世界和这世界的静静思索。这种哲学,不管其本身如何值得称赞,都不能给帝国遭受的苦痛提供医治的良方。
我认为,普罗提诺在他提醒人们注意思考永恒世办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然而在把这种思考当作美好生活的基本成份这一点上却是错误的。沉思,如果它要变得完整和有意义的话,必须与实践连结起来。它必须激起行动,使实际的政治目标受人尊崇。当它被深藏干隐居地的时候,它仅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手段。
代表了罗马文明的最后繁荣的波爱修,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终生献身于公众管理事业,企图教化哥特人的一位国王,结果招致了灾难,被叛死刑。在狱中,他编辑修订了他的伟大著作:《哲学的慰藉人在该书中,他以一种奇迹般的乐观的理性态度——就仿佛他仍是一位强有力的执政官似的——表明了自己的沉思的快乐,对美好世界的欣喜以及对人类的希望,因为人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未将他遗弃。在整个黑暗时期,他的著作被人传诵着,并且一直流传到古代世界的最终纯粹化了的遗产——一个更为幸福的时代。
我们时代的圣人们有着同样如此行动的义务。巩固那些使我们的时代变得伟大的成就、希望和理想,乃是他们对后代的不可推辞的责任——率直诚恳地研究它们,以使它们象黑暗中的灯塔一样,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人类生活的两个极为木同的概念正在互相斗争,以便夺取对这个世界的统治权。在西方我们看到个体生活对于人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伟大的社会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获得各自的幸福、自由、创造性。我们从不认为个体应该相类似。我们相信,社会的一曲交响乐,各种不同的演员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各自拥有不同的表演器具,并且其和谐来自于一种有意识的共同目的。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自豪之处。他应该具有他自己的良知和目的,除非已经显示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性后果,否则他便应该自由地发展这些良知,达到这些目的。我们极为重视消除痛苦和贫困,也重视知识的增长以及美和艺术的创造。对于我们来说,政府只是一种便利性工具,而非崇拜的对象。
俄国政府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目的概念。个体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是可以牺牲掉的。只有政府才是重要的,才是神圣的,其自身具有一种利益,这种利益并非由个体利益所组成。这一看法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它从根本上是与基督教伦理相对立的,在西方,这种基督教伦理不仅被基督教徒所接受,也被自由思想家们所接受。在苏联的社会中,人的尊严等于零。
人们常常认为,在那个体现了政府的伟大性的精神似的存在物面前屈膝下跪、卑躬屈节,是正确而恰当的。当某人背叛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并且作为对朋友的瞬间轻率行为的惩罚,他还使他陷入一种对西伯利亚集中营的神秘恐惧之中时;当一位学生,由于他的教师的灌输教导,使他的父母被判死刑时;当一个有着超人的勇气,并同邪恶势力作过英勇斗争的人,被严刑拷打、被无理审讯,并且最终木得不无奈何地承认自己触犯过反对当局的莫洛克式①的权力的罪行时,不管是背叛还是坦白都未能给作恶者带来任何意义上的羞愧,难道会是因为他未曾眼膺于他自己的神性?
正是这一概念,我们必须与之斗争。在我看来,并且在大多数赞赏西方立场的人看来,这一概念,如果得以流布的话,将会把生活赋予的一切价值全部清除,除了大难大堆的卑屈动物之外,什么也没留下。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更大的或者深刻的理由说我们不必与之斗争。但是,如果我们要想赢得胜利——不仅在战场上,而且在人的心中和他的持有的传统中——我们就必须先擦亮自己的眼睛,纯洁自己的心灵,弄清楚我们的价值所在,同时,我们必须象波爱修那样,增强自己应对灾难性威胁的勇气。
当俄国过分低估个体的价值时,在我们西方,却有一些过分提高独立个人的独立性的人。任何人的自我都不能被禁闭于花岗岩墙之中;其界限应该是半透明的。智慧的首要步骤,正如在道德中一样,乃是尽可能地打开自我之窗口。许多人发现,把他们的孩子包括进他们的意愿中,并不存在什么困难。在稍许弱小些的程度上,他们还包括了自己的朋友,在危急的时刻甚至也包括了自己的国家。很多人觉得,损害他们国家的东西也损害了他们。在1940年,我知道许多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却遭受了亡国之痛的法国人,其痛苦之状宛苦遭受了截肢之痛。但这还没有将我们的同情心增强到足够容纳我们自己国家的程度。如果世界永远充满了和平,我们就有必要学会以一种与我们现在对待我们自己的同胞的同样的同情态度,容纳进我们全部的人类。并且,如果我们想在艰难时刻保持平静与理智,我们的头脑要是能包含进过去与未来的所有时代,这将是极有助益的。
对于我们的价值概念来说,再也没有比思考一下人类从他的蒙昧而艰难的起步逐渐进化到现在的优越地位,更令人清醒明白了。人当他第一次出现时,乃是一个数目稀少而被追猎的动物,他不如鹿儿轻巧,不如猴儿敏捷,无法抗拒野兽的侵袭,没有抗拒雨水和寒冷的温暖皮毛,没有稳定的食物以供采集;他没有武器,没有驯兽,没有农业。
他唯一拥有的优势——智力——给了他安全。他学会了使用火、弓箭、语言、驯兽以及最终才学会的农业。他学会了在团体中的合作,学会了建造巨大的宫殿和金字塔,学会了开垦四方的世界,并且最终学会了对付疾病与贫穷。他研究星象,发明了几何学,并且学会了以机器代替必要的体力劳动。其中许多重大进步乃是最近的事,并且仍然只限于西方国家。
过去的日子里,许多孩子夭折在摇篮里,成年人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并且在每个国家,人口的绝大部分还是忍受着可伯的贫困的折磨。现在,某些国家已经成功地保护住了绝大部分婴儿的生命,极大地降低了成年人的死亡率,并且几乎消除了可怕的贫困。其他国家,即那些疾病和贫困猖狐的国家,通过采用同样的方法,可望达到同样的发达水平。因而,人类还有新的希望。
除非邪恶现象的根源得到理解,否则我们是别指望认识到这种希望的。但我仍必须强调这一希望。现代人是他又己的命运之神。他之所以遭受这些遭受,是因为他愚蠢或怯懦,而不是因为这是天命注定的。人只有抓住了近在手边的武器,他才可能获得幸福。
我们这些西方世界的人,面对共产主义的恶意批评,显得过于谦卑、过于保守。自从生命出现以来,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进化机制就包含了残酷的折磨、无止境的生存抗争。以及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最终的饥饿死亡。这是动物王国的天然法则,并且直到最近的几个世纪里,也是人类的天然法则。如今,某些国家最终发现了摆脱可怕的贫困的途径:发现了防止末成年人死亡所带来的痛苦、忧伤和无谓的浪费的途径;还发现了用智慧和爱心代替自然的盲目无情的途径。
已经有了这些发现的国家是人类未来的托管人。他们必须充满对新生活方式的勇气,必须使自己保持清醒,不被半开化文明的口号,搞得茫然无措、神情紧张。我们有权力希望,这全是理性的,能够被详细证明的,和能够用统计数据加以陈述的。如果我们让自己由于那些非理性的梦魔丧失了这些希望,那就是对人类的背叛。
如果我们前面是艰难岁月,当这岁月久驻不走,我们必须牢记人类的漫长进化史,这段历史是混乱退步交错的历史,但它的结果总是重新恢复进步的运动。斯宾诺莎是最聪明的人之一,他曾经严格遵守他的智慧的教学生活,主张人应该把过去的事情看作是“永恒的一个方面”。那些懂得如此看待的人将会发现,痛苦的现在比起不如此看待来要容易忍受得多。他们将把它看作是过眼烟云——一个已被解开的结,一条已被跨越的河。自己弄伤了自己的孩子哭得眼泪滂论,似乎世界除了悲伤再也没有其它什么,这是因为他的心灵仅仅限于当前。从斯宾诺莎那儿学得了智慧的人能够把哪怕是不幸的时刻也看作是人类历程的短暂起伏。并且人类本身,从他的蒙昧起源到它的未知结局,也只木过是宇宙历程的短暂插曲。
我们对于其他地方发生的事并不知晓,但要说宇宙包含的东西,再也没什么比我们的好,这却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随着智慧的增长,我们的思想获得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更为宽广的视野。婴儿以分为单位生活,少年以天为单位生活,本能的成人以年为单位生活。富于历史感的人以世纪为单位生活。斯宾诺莎使得我们既不以分、天、年为单位,也木以世纪为单位,而是以永恒为单位生活。学会了这一方法的人将发现,它驱散了不幸的虚幻因素,阻止了随可怕的灾难而来的疯狂倾向。斯宾诺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仍在向他的房东讲述着风趣的故事。他曾写道:“聪明人考虑死亡比任何东西都少”,并且他一直恪守这一箴言到生命的结束。
我并不是说聪明人应该冷漠无情——恰恰相反,他应该比那尚未摆脱个人焦虑的人更加热爱友情、仁慈和同情。在他与其他人之间他的自我不是一堵墙。他将像佛阳一样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会感到痛苦——比起自我主义者来,这是一种更加宽广和深沉的痛苦——但他不会发现这种痛苦不可忍受。他不会受这种痛苦的驱使以至于创造出一系列舒心宽情的好故事,保证再也不会有其它的不幸发生。他不会丧失冷静和自制能力。正如米尔顿的撒旦,他会说:
灵善守其位,在其中天堂就是地狱,地狱就是天堂
首要的是,他会牢记,每一代人都是后世子孙的精神和道德精华的托管人,这些精华乃是人类世世代代逐渐积累而成的。忘记人类的荣耀是很容易的。当李尔王濒临疯狂边缘时,他遇到了假装痴癫、只穿一条毛毯的艾德加。李尔王当即说教道:“别扭扭捏捏。除了象你这样的贫穷、赤裸以及双脚叉立,人再也没有什么。”
这只是真理的一半,另一半被哈姆雷特说了出来:
“人是一件多么完美的作品!理性是如此崇高!能力是多么无限!行列与行进是多么快速,多么值得羡慕!行动多象天使!智慧正如神灵!”
苏联人卑躬屈膝,不惜背叛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以便延缓一下被屠杀的命运,是很难适合于哈姆雷特的话的,但哈姆雷特的话却适合于他们。这适合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中的任何人都能拓宽自己的心灵、释放自己的想象力以及撒播自己的爱心和仁慈。并且只有这样做的人才会最终受人尊敬。东方崇信佛陀,西方崇信基督。他们两人都把爱说成是智慧的谜宫。基督的俗世生活年代与泰伯琉斯帝王是同时的,后者把一生用于残暴和淫逸。泰伯琉斯拥有力量和权力;在他的生活中千千万万的人对他毕恭毕敬。但历史学家们却忘记了他。
即使在有生之年默默无闻,但只要生活得高贵,他就不用担心自己白向世间走一回。从他的生命中放射出某种光辉,这光辉照耀着他的朋友,邻人前进的路程——也许永不熄灭。我发现现在有许多人,总被一种无能的感觉所压抑,并且感到在庞大的现代社会面前个人所能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这是错误的。个人,如果他能对人类充满爱心、保持宽广的视野、富于勇气和坚韧,就大有作为。
按照地质年代计算,人类在地球上第一次出现到现在还只是一瞬间的事,文明从首创到如今也只是眨眼之间的事。虽然有些人危言耸听,但我们的种类很可能不会完全自动消失。人类既然还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也就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不管他一时遭受些什么,也不管什么样的光彩被遮蔽,他迟早会重新出现,也许在一段时间的精神休眠后变得更加强劲,更加富有活力。宇宙广漠无垠,人类只是它的并不重要的一颗行星上的些微点缀,但我们越认识到自己在宇宙力量面前的短暂和无能,就越能为人类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感到震惊。
正是这些可能的人类成就才是我们最终的忠诚所在,并且正是由于这一想法,我们喧嚣的世纪中那些短暂的挫折才变得可以容忍。许多智慧尚待学习,而且如果它们只有通过不幸才能习得,我们就必须以我们最大的坚韧毅力努力去容忍这些不幸。但如果我们马上就能够获得这些智慧,不幸就是不必要的,人类的未来也许就会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幸福甜美。四、没有恐惧的生活
曾经使我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由于一度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恐惧,人类并未从新的科技中得到益处,这些科技,如果被明智地加以运用的话,本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恐惧使人在人类行为的三大领域内变得极不明智,这三大领域就是:对待自然的领域,对待他人的领域,对待自我的领域。在本文中,我希望考察一下如果我们摆脱了古代恐惧的统治,我们的世界如何变得更加美好的各种方式。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开两种恐惧,一是作为一种情感的恐惧;二是作为一种知识的对危险的理性把握。当危险确实存在时,如果对此毫无所知,那将是十分愚蠢的;但是靠恐惧而不是靠理性把握,则很难有效地应付危险的情况。恐惧是我们与动物共有的反应。它是本能的、突然的。有时它起着自我保护的作用,但有时它却起着与此截然相反的作用。没有被恐惧感攫住的人,能够极为明智地发现何种行动能够清除危险。恐惧经常妨碍人们承认他们实际上正在面临着的危险,从而使得他们提不起理智本该提起的警惕。有时,这一情况采取了极为荒唐的形式,例如,对死亡的恐惧有时居然使死者忘了立下遗嘱。明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倒有可能误认为,反对恐惧就意味着反对对真实危险的明确认识。
不同的危险需要不同的应对方式。由于大自然的物理事实的存在,人类不得不屈服于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此程度上人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从我们与他人或者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中也会产生一些妨碍美好生活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由于憎恨或恶意,人们互相之间产生的痛苦是根本不可避免的。从一种负罪感中,人们也为自己造成了无法逃脱的苦难。由于这一原因,对付不同的罪恶的方法也是极不相同的。
大自然强加给人的限制包括食物的限制、原材料的限制以及死亡的生理事实三个方面。但这些都木是绝对的。通过更多的劳动,人们有可能生产出更多的食物;通过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人们可以节约原材料或者利用新的、过去曾被认为毫无用处的材料。死亡可以因治疗和科学的养生术而推迟。但是在这三个方面,虽然我们不能精确地确定限制的界线,限制总还是存在的。再多的药都不会使人长生不老。如果人类连立足的地方都不够,再好的科学都提供不了充足的食物,大自然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这些限制,我们必须科学地加以认识,以便我们在面对它们时,能采取一种导致最少苦难的态度。关于食物问题,解决的方式只能是计划生育。至于原材料问题,答案一半在于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半在于国际性合作,以便防止浪费和保证合理分配。死亡的推迟是医学上的事,但是推迟的意向倒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对此我将在以后再展开讨论。
过去,大自然强加给人的限制常被人以一种迷信的方式加以对待,世上有神灵,也有魔鬼,还有能唤起邪恶精神的巫师;并且如果他们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将引来恶劣天气。时至今日,大主教们还认为干旱和洪涝可以通过祈祷去消除。迷信所要求的各种方式往往助长了邪恶势力。在中世纪,当瘟疫流行时,人们却被召集到教堂里作祈祷;这当然为病毒扩散提供了理想的途径。这些邪恶行为,如果它们真能被根除的话,那也只能由科学来根除。在寻找根除的手段时,促使人们承认罪恶与知识的科学态度本身也有一定的两面性。世界上现在依然还有许多罪恶,它们中最可怕的也许就算人口过剩了。由此可知,大部分哪怕是最发达的国家从总体上说,也是缺乏科学精神的。
对他人的恐惧,就我们已知的角度看来,常常是极为顽固的病症,也就是说我们总以为世上有一些人,只要他们做得到,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伤害我们。然而就算这是真的,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靠恐惧来阻止那些对我们有恶意的人伤害我们。如果你曾经豢养过一只狗,而这只狗有着追逐羊群的嗜好,你就会发现,即使它在羊群静安不动时会显得温文尔雅,但只要羊群开始跑向远处,它就再也不能抗拒诱惑。在这方面,我们中的许多人象狗,也有许多人象羊。我曾经看到过一次在一只丹麦种大狗和一只只有三周大的小猫之间的纯粹心理遭遇战。小猫停在老地方,口中发出呼喀呼啃的怒吼,全身毛发直立。那只丹麦种大狗头脑中想的是什么,我并不知道,但它的行动似乎表明他认为小猫有一种超自然的保护力。在一阵作腔作势之后,它把自己的尾巴夹在两腿之间,然后转身溜走。如果你具有这只小猫般的勇气,面对一连串的攻击,你将会有效地保护好自己,否则的话,你将蒙受这种攻击造成的苦难。但是,这种行为常常只是动物才能做到的,而我更加关注那些只有人才能作出的行为。世上许多攻击都是由于恐惧引起的。我们之所以对自己的邻居发怒吼,只因为害怕他攻击我们:他之所以对我们发出怒吼,原因也只不过如此。试图通过友善的表示以免被人攻击,这是并不少见的情况。这也是非抵抗主义学说的真理成份。对于这种学说,如果它采取的是一种纯粹理论的和绝对的形式,那我是不同意的,但它确实包含了相当大的实践智慧成分,虽然大多教的人并不如此认为。我认为,每一个并不显示攻击性意向的人,能够在消除他人具有的一些攻击性意向方面,做一些事情。即使是行为方式的外在准则在这方面也会有着良好的影响。然而,一旦非攻击性深深地扎根于人的性格之中,它的影响就会比它仅仅从传统准则中产生出来所达到的影响大得多。
不管什么时候,一旦日夜担心的危险真的来临,强烈的恐惧笼罩我们时,需要做的往往有两种不同的事情:一种是,造就一种坚毅品格,使得我们能平静地面对可能到来的不幸;另一种是,按照一种能使危险得以消除的方式改良社会制度。例如,这种方式就可以被用于对付贫困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所有竞争的国家中非常普遍,并且很深蒂固。绝大多数看起来无论怎么都是健全的人,却对金钱有着一种完全是非理性的态度。总有那么一些人,虽然他们很愿意开大额支票,却不肯放弃使用散钱付账,而宁愿受到那些还没有闹翻的传者的冷眼。有一类恐惧,即使在大量彻底的成功之后,仍然难以消除。要防止这类恐惧,需要做的往往有三种不同的事情。第一种是纯粹斯多葛式的方法,这种方法劝慰人,要他平静坦然地面对不幸,哪怕不幸真的降临,也不要使它们占去自己过多的心神。另一种方法是告诉他,他很可能不会受到贫穷的威胁;温和一点的话,这可以通过经济学观点来作论证;极端一点的话,则可以通过精神疗法来进行。最后一种方法则是政治性的方法,它通过政治手段去对付整个贫穷问题,使它不再成为一个不幸的问题。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应该追随所有以上这些方法。在确实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斯多葛式的方法也木妨一试,但是,即使一个人有面对不幸的坚强勇气,如果能够避开不幸,那当然更好。很明显,当恐惧达到一种可怕的程度时,它往往产生于那种真实的不幸并不少见的社会里。因而,那种仅与个人有关的方法虽然也能显示出它应有的效用,但却无法代替那种通过政治手段彻底消除罪恶的方法。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人对勇气抱有如此大的热情,以至于往往为有机会锻炼这种勇气而欣喜莫名。这是荒唐的。你也许会钦佩一个忍受了长期的疾病之痛苦折磨而毫无怨言的人,但如果他能享有更为健康的体魄,这显然好得多。你也许会敬仰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但如果他没有牺牲,事情会好得多,在这一点上,斯多葛派难免会受到责难,因为他们过分看重了忍耐,以至于使得残酷看起来也是一种善,因为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是最高的善的东西来说,残酷是达到这种善的必要的手段。人们往往习惯于赞赏穷人们的高度的忍耐力,但这已是在他们获得选举权之前的事了。
在个人生活中,个人在面对社会时往往充满了恐惧,这种现象在英国格外普遍。人们拼命压制自己,不让自己过于草率而受到伤害。他们尽其所能地把感情专注于自我身上。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只要他们无意于自私地欺骗你,他们就会严格地按照你的方式行事。他们死板教条、软弱胆小、消极被动。他们身被一层特制的盔甲,以便把吓坏了的孩子们隐藏起来。结果是,社会交往变得繁琐沉闷,友谊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踪无影,爱情也变成了它本该具有的东西的灰色阴影。人们喜欢引证布朗宁的一段句子:
感谢上帝,是你创造了这难以伺服的家伙
化自诩心灵有两面,一面面对俗世生活
一面向他心爱的女人炫耀。
我并不是一位心理分析专家,但我想,如果我真是的话,我就能讨论一下布朗于的这种感激之情了。他用以面对世俗生活的那一面心灵乃是这样的:他感到他能开辟这块生活的荒原,而用不着害怕受到伤害;在其中没有嘲弄奚落,也没有导致痛苦的知识。其心灵的另一面,即向他心爱的女人炫耀的那一面,包含了全部的虚荣、自负和夸夸其谈,一旦面对同一个俱乐部里的男人时,他就再也不敢炫耀了。后一面同前一面一样,都是恐惧的结果,因为前一面阻止任何新鲜气息进入到他的自我框架中,除非互相吹捧,这心灵是谁也不允许进入其中的。外部世界是苍白黯淡的,内部世界则是固步自封的。这并不是人际关系所应有的状况,人际关系应该是自由的、自发的。虚荣心应该少一点,嫉妒心应该淡一点。固步自封的习惯不仅很容易使自我欺骗暗中滋生,而且,由于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纯粹消极的自我形象的保护上,因而极大地减少了用于好的方面的精力。这种习惯还有一个更大的缺陷,这就是,它使人更倾心于掩盖起自己的友谊冲动,因为一旦这种冲动被人发觉,就会使他们感到自己非常脆弱。短时的单调沉闷以及长期的思想僵化,就是这种社会性恐惧的统治结果。
我并没有把无恐惧的世界想象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在某个方向,它是自由的,而这个方向正是现在所限制的方向。在另一个方向,现在有着自由,却正是它试图加以立法的方向。以后,将有一些法律来调整食物供应和原材料分配。而首要的是,将有一部专门用来阻止战争的法律。我还想,除非在教育的过程中人们注入了某种东西,否则,一个没有过分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社会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当人的属性受到关注时,才会有科学的道德准则存在,这一准则就是:一种试图弄清事实真相,并在弄清事实真相后坦然予以承认的习惯,如今的世界充满了各种感伤主义者,他们在发现不利的事实时,仅仅简单地拒绝承认了事。思维的这种习惯能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因为不利的事实,在它们还没有被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有着更为不利的影响。知识准则即主动承认事实的意愿,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达到。当自然力量确实存在时,对之不予承认当然是极为愚蠢的,而这样的自我评价则更是理智的丧失。
由于物质属性的作用,某些只有教育才能造成的习惯,对于我们的生存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不相信一个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会刷牙,确实,一个从小不识害虫为何物的孩子,是不会懂得清洁的重要性的。健康的保持需要物质上的一定的节制,而这种节制,孩子们仅仅通过事后的告诫,是很难懂得的。我认为一定量的节制在教育中是必要的,这木仅仅是为了健康的原因,而且还在于它能造成那些人们对之争议极少的社会行为习惯。我们不会在吃饭时抢走邻居的饭碗,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了不要这样做。在我们长大成熟的很久以前,这种习惯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脑海里,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意识到它。准时吃饭,虽然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但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极大地减少了用在吃饭上的时间和精力。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习惯的养成必须成为早期教育的关键部分。一些现代教育工作者也许给教育带来了更大得多的自由,然而,还有一种自由,也是教育工作应该加以保护的——虽然它现在还未如此实行,这一自由就是我讲的情感自由。保护情感自由的原因有多重:一方面,对情感的过分限制容易使人麻木不仁,并且导致活力的丧失;另一方面,不容许发泄的情感容易变坏,它会寻找一个较之原来被禁止的发泄出口更有害的发泄出口。还有第三种原因,这就是,无论何处,只要一个社会被紧紧地捆绑在传统准则上,许多其实并没有害处的情感也会被认为不可取。因此,我认为,虽然考虑到科学事实,考虑到某些没有了它们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困难的习惯,节制是必要的,但是在教育中,对于情感的节制却是越少越好。首要的是,千万别有这种企图,即引起表达一种很可能是虚假的情感的企图。
过去的教育工作者大相信原罪说了,以至于总认为,孩子们应该被教育成某种与自然状态截然不同的人。这种教育的极端例子,要算圣·奥古斯都关于他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叙述了。拉丁文,他说,他是在母亲的膝下毫无困难地学会的,当然,最后他掌握得很好。希腊文,他是从一位非常严厉的男教师那儿学会的,这位老师动则打人,苛刻之极,结果——他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学好它。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那位男教师教他的方法好,因为——他说——这种方法治好了他的“有害的欢乐”。这一番叙述是教育工作所持观点的再好不过的对立面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看待孩子,应该像一位园艺师看待草木一样,他所做的,就是如何给以适当的土壤和适度的水份,使它们得以成长。如果你的玫瑰花没开放,你不会想到去鞭挞它;而且试图找出在对待它的过程中到底出了什么错。如果你的孩子没有成功,你应该象对待玫瑰花那样去对待他。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而非一种消极的态度。重要的东西是孩子做了什么,而不是孩子没做什么。并且他们所做的,如果确实还有一定的价值的话,必须是他们自身活力的自发表现。如果你拿定了主意,你可以为孩子们准备一种军事生活,告诉他们在听到命令时,全部在同样的时刻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孩子们将会在挫折感中长大,变得发育不全,对世界充满了很深蒂固的愤怒和仇恨——毫无疑问,如果他们想成为一名被雇来杀人的士兵,这种情感就是十分有用钢;然而,如果他想成为一名和平世界的幸福公民,这种情感就不再是有用的东
声明:在澳纽网频道上发表的内容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的目的,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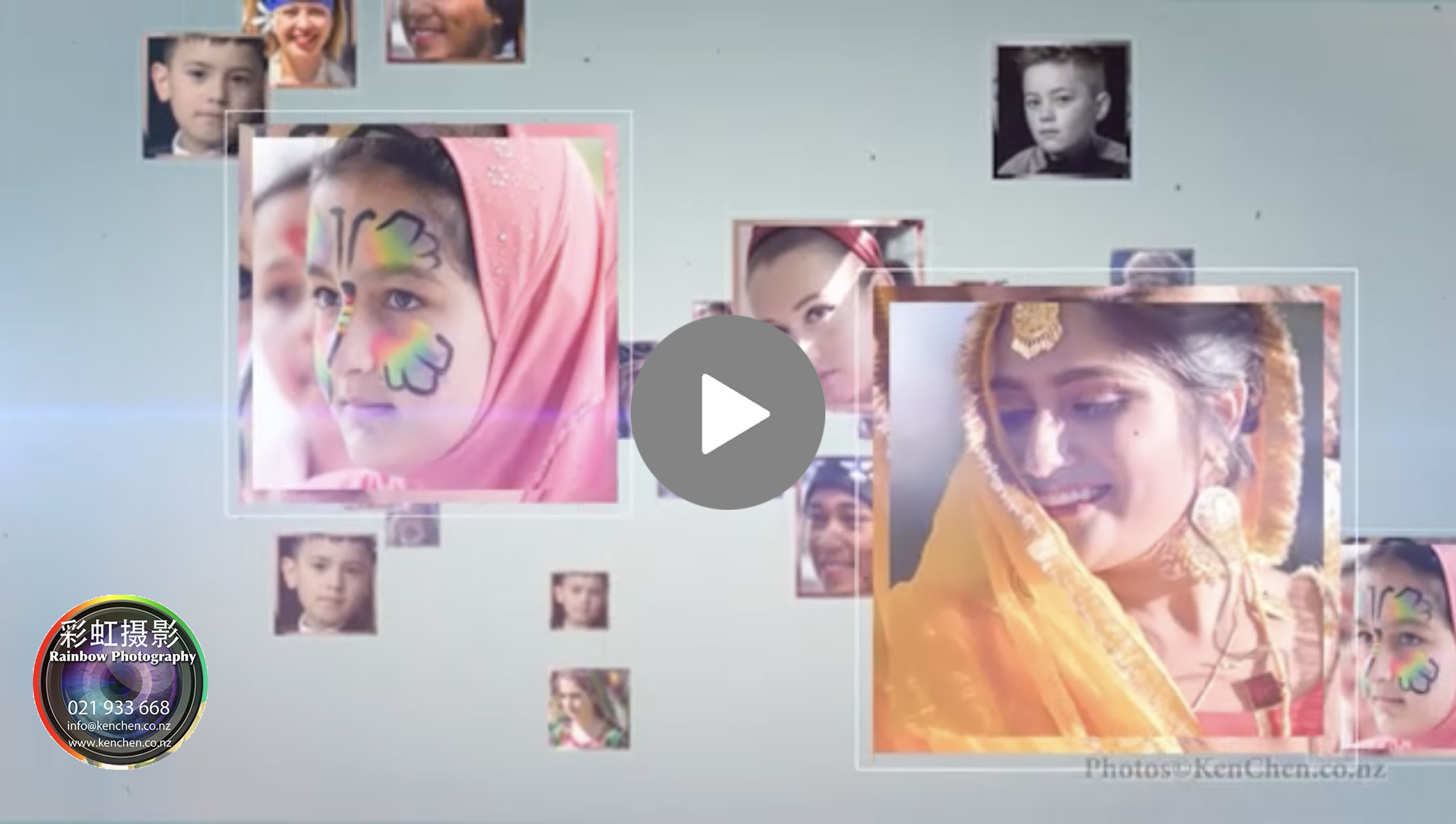



感谢您对澳纽网的支持
